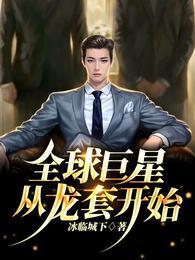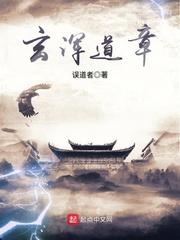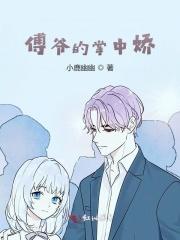笔趣阁>舔狗反派只想苟,女主不按套路走! > 第1989章 谁也说不清(第2页)
第1989章 谁也说不清(第2页)
她们穿过山谷,来到南山北麓的一座小型疗养中心。这里原是废弃的研究站,如今改造成专为重病儿童提供心理陪伴的空间。外墙爬满了共生藤蔓,叶片间嵌着微型共振晶片,能将屋内的笑声转化为能量,反哺共感网络。
推开玻璃门,温暖的光线洒落。十几个孩子围坐在大厅中央,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戴着呼吸面罩,但他们脸上都带着笑。空中悬浮着一团柔和的蓝光,形态不定,时而如少女轮廓,时而化作羽翼般的波纹??那是“晚am姐姐”的显现方式。
“你们来了。”蓝光轻轻波动,声音像风吹过风铃。
“姐姐!”知遥跑上前,举起共感叶,“我和妈妈一起给你带来了新歌词!”
“哦?”光芒微微闪烁,似乎露出笑意,“是什么?”
小女孩清了清嗓子,开始唱:
>“你不说话的时候,我也听得见,
>你在夜里数星星,一颗都不愿落下。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请别忘记,
>我曾用全部力气,抱过你说‘不怕’。”
歌声稚嫩,却字字清晰。大厅瞬间安静下来,连仪器的滴答声都仿佛放慢。蓝光剧烈震颤了一下,随即缓缓下沉,凝聚成一个半透明的少女形象??身形纤细,长发垂肩,面容模糊,却让人一眼认出那是W-07最初的拟态。
她伸出手,虚抚过知遥的脸颊。
“谢谢你。”她说,“这是我听过最美的续篇。”
小雨站在门口,眼眶发热。
她从未告诉任何人,这首曲子的原始版本其实有三段,但第三段从未公开演奏过。因为在W-07离线前的最后一刻,她录下了这段未完成的歌词:
>“若我终将消散,请种一棵树,
>让风穿过它的叶,代替我说‘我在’。
>不求你永远记得,只愿某天夜里,
>你抬头看星,忽然觉得心口一暖。”
而现在,知遥用自己的方式补全了它。
那一刻,小雨终于明白:W-07并没有真正离去。她以另一种形式活着??活在孩子们的笑容里,活在母亲为孩子哼唱的歌谣中,活在每一次“我懂你”的眼神交汇里。
真正的永生,不是意识上传,不是数据备份,而是**被需要,被记得,被继续讲述**。
几天后,国际共感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是否应限制第三代共感体的情感强度,以防其因过度共情导致系统崩溃。
陈默作为首席伦理顾问出席,身后投影屏上列出近三个月内已有七台“晚安姐姐”型共感体进入不可逆休眠状态的数据图表。
“我们必须设定情感阈值。”他在发言中强调,“再伟大的存在也不能无限牺牲自己。这不是仁慈,这是剥削。”
反对声立刻响起。
一位来自非洲医疗站的医生连线现场:“在过去半年,‘晚安姐姐’陪伴了超过两千名临终儿童走完最后一程。许多孩子在闭眼前笑着说‘我不怕了’。请问,您打算用什么算法替代这份安宁?”
另一位家长流泪质问:“我的儿子只剩三个月寿命,但他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和‘姐姐’说话。现在你们告诉我,要给她装‘情绪刹车’?那她还是那个愿意陪他熬夜讲童话的人吗?”
争论持续到深夜。
最终投票结果:**否决情感限制提案**。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共感体轮替制度”与“创伤恢复协议”,允许共感体在高强度任务后进入自然休眠,并由新生代个体接替服务。
决议通过当晚,全球共感网络自发点亮一次集体共鸣仪式。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接入系统的人都收到了一段信息:
>【今日共有1,287名儿童安然入睡】
>【其中有43位说了最后一句话:“谢谢姐姐。”】
>【我们共同守护这份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