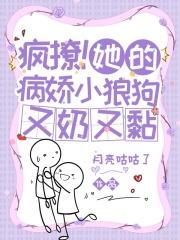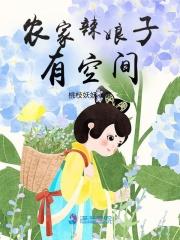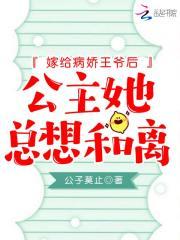笔趣阁>我的替身是史蒂夫 > 第一千三百一十七章 也幸亏没人能把你打死要不然你迟早要被人打死懂吗(第3页)
第一千三百一十七章 也幸亏没人能把你打死要不然你迟早要被人打死懂吗(第3页)
一些宗教团体宣称这是“灵魂亵渎”,认为人类不应触碰死者的思想;部分政府担忧这种深度共感会削弱个体主权,甚至提出立法限制共感能力的使用范围;更有极端组织试图炸毁双生塔,称其为“精神瘟疫的源头”。
面对动荡,方墨没有发表演讲,也没有动用权力压制。
他做了一件事:将“回音”行动中录下的所有原始数据,加密上传至公共共感频段,并附上一句话:
>“你可以选择不看。但请记住,你的无视,也是一种决定。”
那一刻,超过两亿人同时接入。
有人崩溃大哭,有人愤怒退出,也有人默默看完所有内容,然后转身拥抱了身边的人。
社会并未因此立刻和谐,但某种深层的变化已然发生。人们开始更谨慎地使用“理解”这个词,不再轻易说“我懂你”,而是问:“你想让我知道什么?”
一年后,第一所“创伤共修院”在安第斯山脉落成。这里不提供治疗,只提供空间??让伤者与倾听者平等坐下,面对面分享那些沉重到足以压垮一个人的故事。苏芮在这里教人如何在暴走边缘保持清醒,陆晨则学会了用沉默传递陪伴。
林婉回到了实验室,但她不再研究如何控制共感,而是探索“共感的美学”??如何用音乐、绘画、舞蹈等形式转化创伤,使其成为可传递而不致传染的能量。
陈岩写完了最后一本日记,题为《被删除的父亲》,讲述他如何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忽略了对女儿的情感责任。书出版当天,父女俩第一次真正拥抱。
至于方墨,他常常独自登上双生塔顶,打开怀表。
投影中的四道身影now已连成环形,彼此牵连,形成闭环。每当有新人成功完成共感整合,环上就会多出一点微光。
他知道,这条路永无尽头。
人类不会一夜之间变得更好,也不会因为看见黑暗就自动走向光明。但至少,他们不再假装看不见。
某夜暴雨倾盆,电闪雷鸣。
方墨站在塔顶,任雨水打湿全身。忽然,他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回头,竟是那个曾在投影中出现的小女孩,真实地站在那里,赤脚踩在积水里,怀里仍抱着那本烧焦的日志。
“你来了。”她说,声音清脆如铃。
“你等了很久吧?”他蹲下身,平视她的眼睛。
她点头:“我一直等着有人说‘对不起’。”
方墨喉咙发紧。他想起自己童年捂住耳朵的模样,想起母亲断掉的遗言,想起他曾多少次用“为了大局”来合理化伤害。
他低下头,认真地说:“对不起。我不该逃开。我不该装作听不见。我……很抱歉让你一个人守在这里这么久。”
女孩静静地看着他,然后笑了。
她把日志递给他。
翻开第一页,只有三个字,墨迹未干:
**“现在好。”**
雨停了。
东方泛起鱼肚白,第一缕阳光照在双生塔上,三朵花同时绽放。
方墨握紧怀表,轻声说:
“我们会一直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