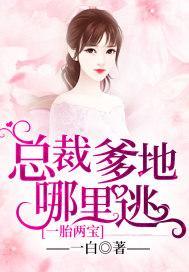笔趣阁>四合院之饮食男女 > 第130章 一朵白莲花(第1页)
第130章 一朵白莲花(第1页)
“未来的事,谁又能说的准呢。”
李学武无奈地笑了笑,摊开手讲道:“您应该了解我们的状况,至少现在还没决定走出来。”
“哦,是嘛??”
什么现在还没决定走出来,你怎么不说没能力走出来呢。。。
春末的槐花落得比雪还轻,一瓣一瓣沾在静语墙的盲文上,像是无声的回应。苏晴清晨五点就到了,她将新一批“迟语库”中的匿名心声导入AI情感模型,试图解析这些压抑已久的言语背后的情绪图谱。系统刚启动,屏幕忽然跳出异常提示:有三十七条信息在输入瞬间自动触发了“共鸣回溯”功能,且匹配源全部指向林秀兰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的一组未编号短诗??那一年,她正因“思想问题”被下放养猪。
其中一条留言来自云南山区的小学教师:“我每天教孩子们唱国歌、背课文,可我自己却不敢说真话。十年前,我举报过一个支教老师,因为他说了句‘这地方穷得连希望都长不出’。后来他被调走,再没音讯。我每晚梦见他在山路上走,越走越远,回头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系统自动匹配出的诗句是:
>“你用沉默喂养谎言,
>它便长得比山还高。
>而真正的罪,
>不是说了什么,
>是明明看见了光,
>却亲手拉上了窗帘。”
苏晴怔住良久,手指悬在删除键上方,终究没有按下。她知道,这些话一旦录入“未来之声”,就会像种子一样散播出去,在某个角落生根发芽。但她也明白,有些伤口揭开得太快,反而会溃烂。
王亚娟推门进来时手里抱着一叠泛黄的信封。“浙江小学送来的雕版复刻样本,已经可以批量印刷了。”她说着放下箱子,“但更关键的是这个??”她抽出一封夹在中间的旧信,“是当年那位印刷厂工人临终前写的遗书。他说,他藏了三百张雕版不假,可还有七张……是从别人手里换来的。”
“什么意思?”苏晴皱眉。
“意思是,”王亚娟声音低下去,“当年不止一个人在偷偷保全文稿。有个女教师,把诗抄在卫生纸上带出审查室;有个图书管理员,用借阅登记簿的背面誊录;还有一个狱警,据说曾帮她传递消息。”她顿了顿,“而这七张雕版的内容,从未出现在任何已知手稿中。”
两人立刻联系文物修复团队,连夜比对材质与刀痕。第二天中午,确认结果出炉:这七块木板上的文字确属林秀兰笔迹风格,内容为一组题为《缝》的组诗,共九首,创作时间标注为1978年冬??正是她短暂平反后又被重新审查的时期。
第一首便让所有人呼吸一滞:
>“他们剪碎我的稿纸,
>我就把碎片缝进衣领。
>线是头发做的,针是铁窗磨的。
>每缝一针,血滴下来,
>就成了另一个字。”
赵建国当场决定立即数字化并公开发布。然而就在上传前夜,系统遭到不明攻击,整段数据险些被清空。幸亏小舟提前设下了物理隔离备份??这位几乎从不开口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为“静语计划”的隐形守护者。他的轮椅旁常年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总写着不同的密码或警告。那天夜里,他用摩斯灯语向苏晴发出了三次“危险”。
事后追查发现,攻击IP竟源自某省级宣传部门的废弃服务器。虽无法证实是否人为操作,但舆论已迅速发酵。社交媒体上掀起激烈争论:一方指责“静语运动”挑战主流叙事底线,企图翻旧账;另一方则疾呼,“如果我们连一段诗都不敢面对,那我们究竟在守护什么?”
压力之下,教育部那位评审委员再度发声,称“文化传承应以团结为导向”,暗示不宜过度渲染历史伤痛。与此同时,几家官媒刊发评论文章,强调“集体记忆需要引导而非放任”。
但这一次,民众的反应出乎意料。
成都那位发起“倾听日”的高中生,在校园广播站朗读了《缝》的全文,并宣布退出市三好学生评选。“如果诚实是一种错误,”他说,“那我宁愿不当模范。”
武汉护士带领的“临终话语守护计划”成员集体签署声明:愿将所有收录的遗言永久接入“迟语库”,哪怕其中包含对体制的控诉。
最令人震动的是,内蒙古那座“静语种子库”所在地的牧民们,自发组织起一支诵读队,每日清晨围坐在沙丘之上,用蒙语轮流吟唱林秀兰的诗。视频传开后,有人听出他们唱的正是那七首从未面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