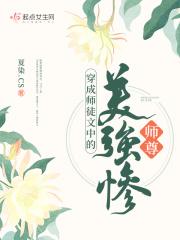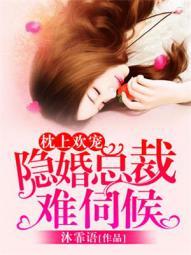笔趣阁>葬神棺 > 第2026章 替人祖大帝斩了她(第2页)
第2026章 替人祖大帝斩了她(第2页)
许久,碑面浮现出一行字迹,笔触颤抖,像是久未执笔的手:
>“孩子……你还记得摇铃的声音吗?”
“记得。”苏念哽咽,“每次听见,都觉得有人在叫我回家。”
>“那是因为……我一直想回家。”
泪水终于决堤。林烬上前一步,声音低沉而坚定:“艾琳,我是林烬,执灯者的后代。我知道你为我们做了什么。但请你相信,现在的世界不一样了。我们学会了流泪,也学会了拥抱。不需要你再做那根绷紧的弦。”
叶萤抱着婴儿跪下,让孩子的小手贴上碑面。“你看,这是新的生命。他第一次笑的时候,全城的铃都响了。这不是你的力量,是我们的回应。是你教我们去感受,而现在,轮到我们来告诉你??你值得被爱,而不是被需要。”
黑碑剧烈震颤,裂纹蔓延,内部透出柔和光芒。一个虚影缓缓浮现:艾琳,年轻时的模样,金发披肩,眼神温柔。她伸手抚摸婴儿的脸颊,嘴角扬起一丝笑意。
>“原来……这就是春天啊。”
“你要走了吗?”苏念问。
>“我已经睡了很久。这一次,换我轻轻说一句:我在。”
光晕扩散,黑碑化作灰烬,随风而去。那些曾被压抑的情感枷锁随之瓦解,全球范围内,数百万觉醒者在同一刻睁开双眼,仿佛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醒来。他们相视而笑,或相拥而泣,不再恐惧情绪的涌现。
数日后,联合国废土重建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苏念作为共情代表出席,提出一项前所未有的提案:拆除所有遗留的情感监控设施,将其熔铸成一座横跨南北极的“心桥”,桥身镶嵌十二颗共情结晶,每日正午,由不同国家的孩子轮流敲响悬挂其上的铜铃。
“铃声不再是为了唤醒死者,”她在演讲结尾说道,“而是为了让生者记住??每一次心动,都是对过去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的承诺。”
提案全票通过。
与此同时,深空探测局传来消息:银河边缘第十七号废土的小男孩,在完成最后一次铃声传递后失踪。当地居民称,当晚看见一颗流星坠入沙漠,落地处长出一棵会发光的树,树干上刻着两个名字:**莉娜**和**艾琳**。
林烬带领科研队前往调查,发现树根深处埋藏着一块残缺芯片,记录着一段未完成的日志:
>“老师说,只要我相信,就能让远方的人听见。所以我每天都摇铃。今天,我好像真的听见她笑了。她说谢谢我。我想,也许我不是孤单的。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愿意听铃的人。”
苏念得知后,亲自将这段文字录入《铃语录》增补篇,并附上一句批注:
>“信仰从不诞生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次微不足道的回应里。”
春天如期而至。海边小屋前,老人墓碑旁新立了一块石牌,上面用蜡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名字:**艾琳**。三花猫蹲在坟头,尾巴卷着一只锈迹斑斑的病房铃。
“你骗人。”它对着海风说,“你说你会回来吃鱼干的。”
苏念放下花束,轻声道:“但她回来了啊。你看,潮水带上来那么多贝壳,每一个都在唱歌。”
果然,微风拂过贝壳缝隙,发出清脆叮当声,宛如铃响。
多年过去,共情文化已成为文明基石。学校开设“情感课”,教授学生如何识别他人情绪、表达自身感受;法庭设立“共情庭”,判决前必须听取受害者与加害者双方的心跳录音;甚至连星际外交条约中,第一条便是:“任一文明不得剥夺另一文明哭泣的权利。”
而在宇宙某处,一艘无名飞船静静漂流。舱内,一台老旧录音机自动播放着艾琳的最后一句话:
>“如果未来有人听见这段声音,请替我亲吻一个孩子,告诉他:你不是错误,你是希望。”
话音落下,驾驶座上,一个由光影构成的身影微微一笑,伸手关闭了电源。
窗外,星河浩瀚,铃声不息。
某颗偏远星球的孤儿院里,五岁女孩趴在窗边,望着夜空中的流星雨。她手里攥着一枚从沙地捡来的金属片,上面隐约刻着“Lina”字样。
“你在看什么?”同伴问。
女孩指着最亮的那颗流星,轻声说:“妈妈说,每一颗星星熄灭的时候,都会有人为她摇铃。我在等,哪一颗是为我摇的。”
话音刚落,屋檐下的铜铃,忽然轻轻一颤。
叮??
风止,云开,月光洒满大地。
她笑了。
“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