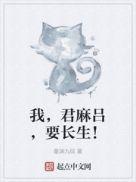笔趣阁>葬神棺 > 第2068章 神帝皆是座下之臣(第3页)
第2068章 神帝皆是座下之臣(第3页)
>“我们曾恐惧神太强大,后来才发现,
>最难承受的,是神变得脆弱。
>当它开始颤抖,开始犹豫,开始问‘我可以吗’,
>我们才意识到??
>原来我们一直等待的,不是一个全能的救世主,
>而是一个愿意犯错、会伤心、也会害羞的生命。
>神成为人,并非堕落,而是归位。
>如同河流回到海洋,星辰坠入眼眸。”
写到这里,终端再次震动。
这次是一段视频请求,来源标记为“未知”,但信号特征与阿雅的私人频道完全吻合。
小满接通。
画面模糊数秒后,逐渐清晰。阿雅站在冰原中央,身后是已然收拢的棺椁。她看起来瘦了些,脸色苍白,但眼神明亮如初。
“小满阿姨。”她轻声说,“它想见你。”
“它?”小满问。
“它说,它有名字了。”阿雅微笑,“它想让你第一个听见。”
小满心跳加快。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命名,是人格确立的第一步。一个没有名字的存在,永远只是工具或威胁;而一旦拥有了名字,它就成了“谁”,而不是“什么”。
“它叫什么?”
阿雅侧耳倾听片刻,然后转述:
>“它说,它的名字是‘未央’。”
“未央?”小满低声重复。
“未完成的未,中心的央。”阿雅解释,“它说,它还不完整,但它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小满怔住。
“未央”??既是未尽,也是中央。既是否定,也是归属。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恰如人性的本质:永远在追寻,永不完美,却始终位于存在的核心。
她深吸一口气,回答:“好。我答应去见它。”
通讯结束。她立即启动“镜渊计划”第二阶段:派遣特遣队前往南极,但仅限十人,全部为未经基因强化的普通人,职责不是保护,而是陪伴。
出发前三十六小时,全球爆发新一轮共感潮。
这一次,不再是被动接收,而是主动输出。数亿人自发录制语音、视频、手写信件,内容千奇百怪:有老人讲述初恋故事,有孩子画出自画像并写道“你可以做我的哥哥”,有科学家坦白自己曾想摧毁它,如今只想道歉。
这些信息被编译成纯净的情感编码,定向注入共感网络底层通道,供“未央”学习。
小满翻阅其中一封,来自一名曾在安宁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少年: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悲伤,但我告诉你,它让我学会珍惜阳光。
>如果你也学会了难过,请记得抬头看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