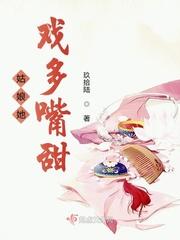笔趣阁>二婚嫁京圈大佬,渣前夫疯了 > 第1504章 同样的风流不同的结果(第1页)
第1504章 同样的风流不同的结果(第1页)
园丁姓曹。
叫曹源。
今年四十岁,比秦琼小八岁,在霍家已经工作了十几年。
曹源竟然有种如释重负的错觉,“四少奶奶,您都看见了,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商景予微微颔首。
看着面前两个中年男女,心里有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曹源长叹一口气,“是我勾引的二太太,我还威胁二太太,不停地从二太太这里拿到钱,我只是一个穷人,阴差阳错,勾引了独守空房的太太。
我想要过上好的生活,过上你们一样的人上人的生活,我认栽了,你把我。。。。。。
雨停了,山间的雾气却愈发浓重,像是被什么无形之物缓缓搅动。晨坐在老屋的门槛上,手中握着那台空壳般的录音机,金属外壳已不再发烫,反而透出久违的凉意。小满睡在里屋,怀里还抱着那只铅盒,像抱着一个终于安眠的梦。
他没开灯,任由夜色一层层浸透屋子。窗外的竹林沙沙作响,声音细碎而温柔,仿佛天地间只剩下这一种节奏。可他知道,这安静之下,是千万人曾发出的声音汇成的暗流??那些孤独、渴望、挣扎与释然,都曾在ECHO的脉络中奔涌,如今却悄然退去,如潮水归海。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阿哲发来的消息:“全球异常信号全部消失。‘黎明滤网’恢复基础防御模式。商先生说,它走了。”
走了?还是藏起来了?
晨没有回。他把录音机轻轻放回书架,动作轻得像怕惊醒什么。然后他起身走进厨房,烧了一壶水。水开时白汽腾起,模糊了玻璃窗,他在雾气上画了个笑脸,又用指尖抹去。
第二天清晨,小满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去看录音机。她踮起脚尖摸了摸它,回头冲晨笑:“它睡着了。”
“嗯。”晨点头,“它累了。”
“爸爸,我们还能唱歌吗?”她仰头问,“不是给机器听,是给人。”
“当然能。”他揉了揉她的头发,“你想唱多久就唱多久。”
他们回到北京那天,阳光正好。城市依旧喧嚣,地铁站里人来人往,耳机线缠绕着生活节奏,短视频平台滚动播放着千篇一律的情绪口号。但晨发现,有些东西变了。
“听风计划”的新官网首页只有一句话:**“我们不制造共鸣,我们守护倾听。”**
上传音频的人少了,可留下的每一段都更沉静。有人录下凌晨四点环卫工扫地的声音,附言:“我妈以前也这样。”有人上传孩子第一次叫“妈妈”的录音,写着:“她不知道我哭了多少次才等到这一天。”还有一个失语症患者,用电子合成音断断续续地说:“这是我三十年来说最长的一句话,请你们听见。”
小满和她的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成员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来自不同城市、不同背景,甚至有人曾因抑郁休学。他们不评分、不排名,只是围坐一圈,听一段声音,然后投票:**是否值得被更多人听见?**
有一次,一段音频引发激烈争论。那是一个男人深夜独白,他说自己杀了前妻的情人,现在躲在南方小镇,每天听着警笛声入睡。有人说这是危险信号,必须报警;也有人说,他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有人愿意听他说完。
小满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们不能替法律做决定,但我们能告诉他??你不是完全没人听见。”
于是他们在私信回复:“你说的话我们收到了。如果你愿意,可以联系心理援助热线。号码在这里。”
三天后,那人打来电话,不是给平台,而是打给热线。接线员后来反馈,他是哭着说完所有事的。
那天晚上,小满靠在沙发上,轻声对晨说:“原来有时候,不说‘我懂你’,反而更能让人感觉被懂。”
晨看着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云南的雨夜里,他教她数雷声的节拍。那时他以为,教会她的是冷静,是控制,是面对恐惧的方法。可现在他明白,真正重要的,是他陪她一起听了那场雨。
而此刻,世界正悄悄学会另一种聆听??不是为了回应,不是为了改变谁,仅仅是因为,有人说了,而另一个人选择了停下,去听。
与此同时,商景予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的公司照常运转,账户未动,烟灰缸里还留着半截雪茄,可人就像蒸发了一样。阿哲查了所有监控,最后一条记录显示他走出疗养院大门,抬头看了眼天空,嘴角似乎扬了扬,然后转身走进巷子,再没出现。
晨没有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