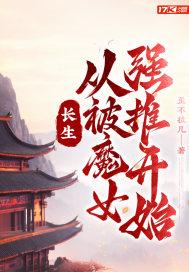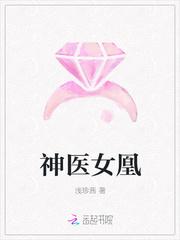笔趣阁>二婚嫁京圈大佬,渣前夫疯了 > 第1537章 父亲若想我联姻我可以(第2页)
第1537章 父亲若想我联姻我可以(第2页)
>可就在她离开前一周,泥石流爆发。她本可以提前走,但她留下来帮我们转移学生。最后,是小川推了她一把,自己却被卷入洪流……我们找了三天,只找到她掉落的助听器和这枚铃铛。
>小川活了下来,但再次封闭了自己。这些年,每到清明,他都会去后山对着‘声音瓶’说话。去年,他考上了省城的聋哑特教学校,开始学手语。
>他托我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您。他说:‘请告诉念安爸爸,我没有忘记她教我的第一句话??我不是灾后的幸存者,我是爱的传递者。’”**
沈知远读完最后一个字,整个人僵在原地,呼吸几乎停滞。
原来,念安的生命从未真正停止。她在千里之外的群山中种下了种子,那些他曾以为随她一同埋葬的温柔与勇气,早已生根发芽,长成了另一片森林。
泪水无声滑落,滴在照片上,晕开了小川模糊的脸庞。
“我想见他。”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如锈铁摩擦,“我要亲自去云南。”
晨静静地看着他:“我已经联系了当地教育局。下周有公益航班,小满也要去。”
沈知远点头,手指紧紧攥着那张照片,仿佛攥着女儿残存的气息。
三天后,他们启程飞往临沧。飞机穿越云层时,沈知远闭目养神,脑海中反复回响着李老师信中的那句话:“她留下来帮我们转移学生。”
当年媒体指责他冷血无情,为了商业利益放弃出席女儿遗体告别仪式。可没人知道,那天他其实已经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却被董事会强行拦下??一笔关乎集团生死的贷款即将到期,若他缺席签字,公司将面临崩盘。他最终屈服于责任二字,却因此永远失去了最后一面的机会。
如今他才明白,念安用她的选择,给了他最深刻的审判,也给了他最宽厚的原谅。
抵达临沧已是傍晚。小城依山而建,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草木香。他们入住一所乡村民宿,房东是位慈祥的老奶奶,听说他们是“念安爸爸”一行人,颤巍巍地拿出一双绣花鞋垫:“这是我孙女做的,她说要是念安姐姐还在,一定喜欢这个颜色。”
当晚,沈知远辗转难眠。凌晨两点,他披衣走到院中,抬头望星。这里的夜空格外清澈,银河横贯天际,宛如一条通往记忆深处的光河。
脚步声由远及近。
小满走了出来,手里捧着一碗热粥。
“猜到你睡不着。”她轻声说,“还是老规矩,火候刚好,趁热喝。”
他接过碗,热气扑在脸上,模糊了视线。
“你知道吗?”小满坐到他身旁,“妈妈说,姐姐临走前最后一晚,给她发了条语音。她说:‘如果有一天爸爸来找我,请告诉他,我不是怪他不来,我只是希望他知道,我一直都在等他学会听。’”
沈知远喉头剧烈滚动,几乎无法吞咽。
“所以这次来,不只是为了见小川。”小满仰望着星空,“也是为了让姐姐看到,她的等待,没有白费。”
次日清晨,他们前往守望小学旧址。学校已在灾后重建,但后山那片“声音林”被完整保留下来。数十个玻璃瓶埋在土中,瓶身刻着孩子们的名字和日期。最中央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念安亲笔写下的话:
>**“有些声音,耳朵听不见,
>但心会记得。”**
当地教育局负责人带着一名青年前来??正是小川。他已十九岁,身形清瘦,眼神沉静。见到沈知远时,他没有说话,而是缓缓从背包里取出一本厚厚的素描本。
翻开第一页,是念安的笑容;第二页,是她教他画画的手;第三页,是她站在暴雨中指挥孩子们撤离的身影……整本画册,记录了她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天。
最后一页,是一幅未完成的画:一座桥,桥这端站着穿西装的男人,另一端是穿碎花裙的女孩,中间隔着深渊。画纸一角写着一行小字:
>“我想替她说完那句:爸爸,我一直在等你。”
沈知远双膝一软,缓缓跪坐在地。
小川蹲下身,用手语比划:“她说过,爱不是靠说的,是靠做的。我现在是手语老师,教更多孩子说话。我想让更多人听见,那些曾经被风雨淹没的声音。”
沈知远颤抖着伸出手,握住小川的手,用力点头。
那一刻,十年积压的悔恨、自责、孤独如冰川崩解,化作汹涌的暖流冲刷过灵魂的每一寸荒原。
下午,他们在后山举行了一场特别仪式。孩子们带来了新的声音瓶,录下对亲人、对未来的低语。沈知远也录了一段话,声音平稳却沉重:
“念安,爸爸来了。我走过很远的路,摔过很多跤,才终于明白你要教我的事。我不再逃避声音,也不再害怕回忆。我会继续走下去,带着你的名字,你的铃铛,你教会我的每一句‘我在’。”
录音结束,他将瓶子埋进土里,紧挨着念安当年留下的那一排。
返程前夜,沈知远独自来到海边??这座小城虽不临海,但有一处高山湖泊,当地人称之为“天镜湖”。月光洒在湖面,宛如铺了一层碎银。
他坐在湖边,掏出那枚旧助听器,轻轻戴上。
![真千金有读心术[九零]](/img/220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