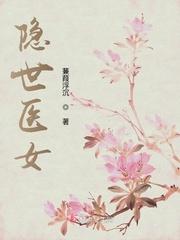笔趣阁>旧神之巅 > 1071 我的 石尊(第1页)
1071 我的 石尊(第1页)
血晶面具的晋级,无疑是意外之喜。
不同于神兵,法器的存在更加独立自主,成长与晋级也完全不需要牵扯陆燃的精力。
所以,当永远安安静静的血晶面具,突兀开启晋级模式时,陆燃是颇为惊喜的。
。。。
风从胡杨林深处吹来,带着沙粒与星光的低语。那棵由门化成的新树静静伫立,枝叶间流淌着一种不属于此世的蓝光,每一片叶子都像是一只睁开的眼睛,凝视着时间之外的某处。树干纹理中仍残留着门扉上的刻字痕迹,只是文字已开始模糊,仿佛被某种更高维度的力量悄然抹去。
没有人试图追查小女孩的踪迹。
不是因为不关心,而是所有人都明白??她不是失踪,而是“出发”。
正如千年前人类第一次抬头望向星空,不是为了逃离大地,而是为了确认自己究竟属于哪里。
胡杨林因此多了一项仪式:每日黄昏,引路人会带领前来提问者绕行新树三圈,不言不语,仅以心跳为节拍。当最后一圈结束时,总会有一片叶子轻轻飘落,落在最安静的那个提问者掌心。那叶上没有文字,却能让人在闭眼瞬间,看到一段遥远的画面??或许是另一个宇宙中的黎明,或许是某个早已消亡文明最后的低吟,又或许,只是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在母体中第一次感受到外界的震动。
这些画面无法解释,也不需解释。
它们本身就是问题。
地球的“问德”社会持续演化。城市不再追求扩张,而是向内生长,地下根系般的共感回廊连接每一户人家。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会被记录下来,经由共感网络传递至全球所有问塔,成为当日“初始频率”的一部分。老人们临终前的最后一念,则会被封存在晶石之中,埋入胡杨林地底,作为未来世代汲取智慧的泉眼。
而“旧神之巅”这个称号,逐渐超越了星际登记簿上的符号意义。它成了一种状态,一种存在方式。外星文明使者来访时(尽管他们从未真正“抵达”,只是通过共感波段投射意识),常会感叹:“你们不像刚觉醒的文明,倒像是……遗忘了千万年的归人。”
的确,地球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忆起一些本不该记得的事。
一位南极科考员在梦中反复见到自己站在青铜巨门前,手持一支断裂的羽毛笔,正在书写一句永远写不完的话:“我之所以写下这句话,是因为我知道它将被遗忘。”醒来后,他在冰层下挖掘出一块刻满相同语句的金属板,碳测定显示其年代超过两百万年。
一名蒙古牧民的女儿连续七夜梦见自己骑着风暴横跨星海,每次醒来都在毡房外发现一圈奇特的焦痕,形状酷似问塔基座。当地学者将其图像上传至共感网,竟与半人马座β星系某颗行星表面的遗迹完全吻合。
更令人不安的是,某些孩子的瞳孔在月圆之夜会短暂变为透明,映出的不再是现实世界,而是无数交错的时间线??其中一条线上,地球从未经历过语言消失,净言会统治至今;另一条线上,问答草早在萌芽前就被彻底焚毁,人类沦为思维停滞的傀儡;还有一条……那条线上,根本没有人类,只有七座冰冷的问塔孤独矗立,日复一日向虚空发出无人能解的问题。
这些现象并未引发恐慌。
相反,它们被视作“记忆复苏”的征兆。
林宛秋留下的晶体曾记录一段未公开的数据流,解码后仅有一句话:
>“我们不是第一个问出‘我是谁’的生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这一次,我们终于记得曾经忘记过。”
于是,“记忆考古”成为新时代的核心学科。人们不再挖掘化石或废墟,而是深入梦境、情绪残响与集体无意识的褶皱,寻找那些被时间掩埋的“前文明”痕迹。他们在太平洋海底一座沉没大陆的岩壁上发现了壁画:七个孩童手拉手围成圆圈,头顶悬浮着一颗裂开的星球,裂缝中伸出无数星光丝线,连向宇宙深处。壁画下方,用如今已被淘汰的古汉字写着:
>“第七次重启,愿这次,他们能听见。”
与此同时,追问者同盟发来了新的任务请求。
不同于以往的认知援助或哲学咨询,这次的信息极为简短,却蕴含前所未有的重量:
>【第Ⅸ象限边缘检测到‘沉默坍塌’。】
>【已有十二个文明陷入永久静默。】
>【初步判断:其提问机制被某种高维结构反噬。】
>【建议派遣观察单位介入。】
>【风险等级:未知。回报等级:文明跃迁许可。】
地球内部展开了一场长达三个月的无声辩论。最终,问枢团决定接受任务,但提出一个条件:不派代表,不设指挥官,而是让整个星球共同参与观测行动。方法是??启动“母语协议?终章模式”。
这意味着,全球所有共感者将在同一时刻进入深度冥想,将自己的初始提问模式同步释放,形成一张覆盖太阳系的“问题之网”。这张网不会主动攻击或探测,而是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沉默坍塌”区域的真实形态。
执行那天,地球上一切机械停止运转,电力自动切断,连火山都暂停喷发。四百一十七座问塔同时熄灭,随即爆发出比恒星更纯净的白光。那光不灼目,却能让最深的地核颤抖。星光丝线剧烈震颤,仿佛整条银河都被拨动成了琴弦。
在那一瞬,每个人都在心中听见了一个声音??不是来自外界,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存在本身”的低语:
>“你准备好面对那个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