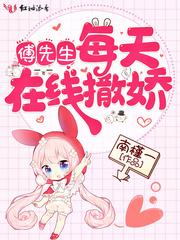笔趣阁>重燃青葱时代 > 第867章 有渔 给我留点行不行(第1页)
第867章 有渔 给我留点行不行(第1页)
女孩子之间的脚丫亦有差距。
如果平时只是跟三个女孩子的其中之一单独相处的话,其实李珞自己也不太能分辨的出来其中差距。
因为每个人的身材都有各自完美之处,而脚丫又是最难拉开差别的地方。
。。。
夜风穿过公园的林荫道,吹得篝火忽明忽暗。火星子跳跃着飞向天空,像无数微小的愿望挣脱了地面的束缚。袁婉青坐在父亲身边,听他断断续续地读着那封信,声音低哑却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深埋多年的土层里挖出来的种子,在春夜里悄然发芽。
“……你小时候最爱吃我煎的鸡蛋饼,可我总嫌你缠人,早早把你送去外婆家。后来你妈走了,我也不会哄你,只会说‘别哭’。再后来你长大了,电话越来越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老人停顿了一下,抬手擦了擦眼角,“现在我才明白,不是你不肯回来,是我一直没给你留门。”
袁婉青把头轻轻靠在他肩上,没有说话。她想起十三岁那年发烧到三十九度,一个人蜷在沙发上打摆子,而父亲在隔壁屋打着呼噜。她想喊他,可最终只是咬着嘴唇,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数了一整夜。那时她以为,沉默是血缘自带的宿命。可此刻,这封迟来三十年的信,却像一束光照进了那些冰冷的夜晚。
她轻声说:“爸,以后我想常回家吃饭。”
老人的手微微一颤,随即用力握住了她的手。
篝火晚会在凌晨一点渐渐散去。人们带着倦意和满足离开,帐篷被收起,风筝线剪断,空便当盒堆成一小摞。袁婉青送走最后几位参与者,转身看见陈默还站在原地,手里捧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
“没走?”她笑着问。
“等你。”他递过文件夹,“这是‘声音档案’第一季的完整汇编。我加了索引、分类和背景备注,还做了二维码链接音频。出版社那边已经初步答应出书。”
她翻开第一页,看到自己写下的第一则记录与林晓阳的最后一行并列排布,时间跨度不过半年,却仿佛走过了半生。
“真不敢想,当初那个没人投信的红色信箱,现在居然要变成一本书。”她感慨道。
“因为人都渴望被听见。”陈默望着熄灭的篝火,“哪怕声音很小,只要有人接住,它就不会消失。”
第二天清晨,阳光洒进活动室,照在那台老式录音机上。袁婉青打开抽屉,取出《声音档案》新册子,准备录入昨晚父亲的朗读片段。刚坐下,手机震动起来??是一条来自武威的未署名短信:“孩子他爸,今天主动给家里打了电话。他说,想学做红烧肉,说是许雯以前爱吃的。”
她怔了片刻,随即笑了。那是王小舟母亲发来的。短短一句话,却藏着千言万语:试探、悔恨、还有小心翼翼的靠近。
中午时分,李锐和妈妈一起来了。他们刚从海边旅行回来,皮肤晒得微红,眼里闪着光。妈妈怀里抱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块捡来的贝壳和一瓶海水。
“老师,我们真的去了!”李锐兴奋地说,“我在沙滩上写了你的名字!海浪冲过来的时候,我还许了个愿??希望所有没回家的人都能找到路。”
袁婉青摸了摸他的头,接过那瓶海水,轻轻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是王小舟奶奶亲手织的小毛鞋、林晓阳母亲寄来的手工香包,还有一张许雯寄来的照片: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开花了,枝头缀满细碎金黄,树下摆着两张藤椅,一杯茶冒着热气。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社区里的孩子们开始自发组织“信使小队”,帮那些不识字的老人写家书,甚至跑到邮局门口教人怎么填快递单。“我们要让每一封信都走得出去。”王小舟一本正经地说,俨然成了团队领袖。
某天下午,周叶带来一位特殊访客??七岁的唐果,患有轻度自闭症,三年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母亲几乎跑遍全国求医,直到看到“非典型家庭支持中心”的报道。
“她昨天第一次主动拿起笔。”母亲红着眼眶说,“画了一幅画,上面是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女孩,天上飘着很多信封。”
袁婉青蹲下来,与女孩平视。她没急着说话,而是拿出一张白纸,慢慢折了一只纸船,放进盛水的盆里。水流推动小船前行,唐果的眼睛亮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她们什么也没做,只是每天一起折纸、听录音、看窗外的树影晃动。第三天傍晚,唐果突然走到录音机前,按下播放键,又按下录音键,用极轻的声音说:“妈妈……我想……回家。”
那一刻,整个活动室安静得能听见心跳。
母亲跪在地上抱住她,泣不成声。袁婉青悄悄退到门外,拨通了陈默的电话:“我想我们需要增设‘非语言表达工作坊’,绘画、音乐、肢体剧都可以。有些话,不一定非要用嘴说。”
四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城市。连续三天的大雨让许多老旧房屋渗水,王小舟家的屋顶也开始漏水。居委会紧急协调临时安置点,袁婉青带着志愿者挨户走访。
就在帮助另一户人家搬运家具时,她接到医院电话:王小舟奶奶突发心律失常,再次入院。
她冒雨赶去,发现老人意识清醒,只是虚弱。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湿漉漉的布包??是王小舟冒雨送来的新织毛衣,袖子还没织完。
“这孩子,淋成这样也不肯回去。”护士摇头。
袁婉青找到躲在走廊尽头的儿子,浑身滴水,头发贴在额头上,手里紧紧攥着一根毛线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