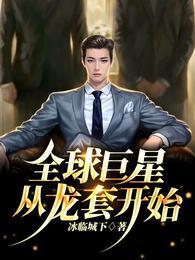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不放纵能叫影帝吗? > 第655章 比我差一点(第3页)
第655章 比我差一点(第3页)
电话那头,阿强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而在这场无形风暴的中心,北京某部委大楼内,一份紧急报告被呈上桌面:
>“监测发现未知短波信号持续传播,内容涉及敏感历史叙述。技术溯源困难,疑似分布式节点网络。建议立即封锁相关关键词,并加强对民间口述活动的管控。”
批复下来只有两个字:**准。**
但命令尚未执行,另一份文件已悄然流转至更高层案头??来自中央党校几位老教授的联名信:
>“真正的稳定,不在于屏蔽多少声音,而在于有多少人愿意主动倾听历史。若连过去的痛都不敢面对,何谈未来的路?建议将‘家庭记忆教育’纳入国情调研课题,探索制度化路径。”
与此同时,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室。
一名戴眼镜的女记者播放了那段烛光直播视频,并提交《火种》项目资料。“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扶贫、环保、科技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但一个国家的伟大,不仅体现在进步的速度,也体现在如何对待自己的伤痕。请问发言人,贵国是否考虑承认公民的‘知情权’与‘记忆权’作为基本人权之一?”
会场鸦雀无声。
良久,中国代表起身,语气平和却坚定:“我国始终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文化权利与历史认知自由。目前已有多个地方试点开展民间记忆传承工作。我们将继续在法律框架内,探索符合国情的历史教育模式。”
掌声稀疏响起。
而在云南山村,新的变化正悄然发生。
教育部派出的专家组抵达村庄,参观记忆学堂,翻阅手抄本,听取村民讲述。带队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司长,全程沉默寡言。临走前,她单独留下时宁,问了一句:
“你觉得,什么样的历史才算安全?”
时宁反问:“您小时候,听过您父亲讲过去的事吗?”
女人怔住,眼神微闪。“没有。他说,忘了最好。”
“可您还记得吧?”时宁轻声说,“哪怕一句都没听清,那种沉默本身,也是一种记忆。”
司长久久未语。离开时,她悄悄留下一本内部参考资料,封面印着几个小字:《关于口述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研究(征求意见稿)》。
春天进入尾声,山花渐谢,新叶繁茂。
又一场雨落下,不大,细细密密,如丝如织。
时宁独自坐在院中,听着雨打酸菜坛的声音。忽然,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站在门口,浑身湿透,面容憔悴,却目光如炬。
她猛地站起,喉咙发紧。
“周秉正?”
他点点头,嘴角扬起一丝疲惫的笑:“我回来了。不是英雄,只是一个还没倒下的人。”
她没有扑上去,也没有流泪,只是转身进屋,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酸菜汤。
“先吃饭。”她说,“别的,明天再说。”
他接过碗,双手微微颤抖。喝下第一口,忽然闭上眼。
“还是这个味儿。”他低声道,“我妈的味道。”
那一夜,他们没谈政治,不讲斗争,只聊童年,聊逃亡路上啃过的野菜,聊曾在雪夜里共用一条毯子取暖的陌生人,聊那些没能活到今天的朋友的名字。
黎明前,周秉正拿出一个U盘。“这里面有蜂巢最后十年的所有备份数据。不止中国的,还有朝鲜、越南、东欧多个国家的秘密档案。它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权,只属于人类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