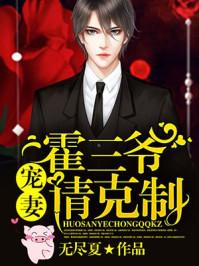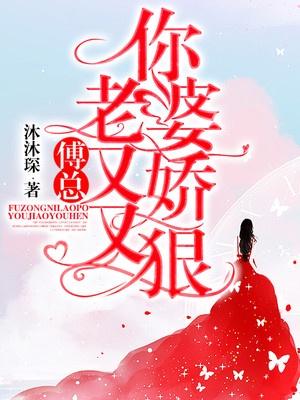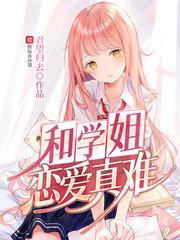笔趣阁>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 第679章家破人亡不亡为九八大卡的白银加更(第2页)
第679章家破人亡不亡为九八大卡的白银加更(第2页)
“什么意思?”旁边的技术员不解。
“有了这些人的信息,就可以逐个施压。”江辰眼神冰冷,“比如告诉某个村干部:你侄子参加了非法培训,影响村里评优;或者通知家长:孩子学的东西没用,别浪费时间。温水煮青蛙,比查封更狠。”
他掏出手机,给公安部网络安全局的朋友发了一条加密消息,并附上日志截图。
三天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通报,称破获一起针对公益教育平台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案件,初步查明背后存在利益集团操纵痕迹,相关线索已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核查。
舆论再度沸腾。“灯塔”微博评论区涌入大量留言:
“原来真的有人怕老百姓学会用电脑。”
“我就是凉山的,谢谢你们没放弃我们。”
“请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妹妹靠你们的编程课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江辰没有回应任何声音。他在等另一件事。
八月中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闭门研讨会,邀请十家社会组织代表就新型职业能力评价制度建言献策。“灯塔”赫然在列。
出发前夜,林小雨找到江辰:“你知道这次会上有多少人希望你失败吗?那些靠认证考试收报名费的机构,那些垄断师资培训的协会,还有……某些习惯了审批权力的部门。”
“我知道。”江辰整理着演讲材料,“所以我不会讲理想,只讲数据。”
“万一他们打断你呢?”
“那就让事实说话。”他抬起头,笑了笑,“你说巴图的故事够不够动人?一个牧民自学成才,反过来教五百个同行识别病羊。他的成果能写进论文,能申请专利,为什么就不能算‘职业技能’?”
林小雨怔住了。她忽然明白,江辰早已不再是那个愤世嫉俗的重生者。他学会了在体制的语言里战斗,用对方的逻辑撬动僵局。
北京,会议如期举行。
当江辰走上讲台,展示出一张张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照片时,会场起初安静得近乎冷漠。直到他播放那段视频:贵州雷山的苗族妇女站在自家银饰工坊门口,用流利的英语接受海外客户视频会议;山东菏泽的残障青年坐着轮椅走进市政府会议室,指着APP上的盲道缺陷要求整改;黑龙江老张穿着护林服,在雪地里操作无人机拍下盗伐现场……
一名白发老专家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江辰的声音平稳而坚定:“各位领导,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敢不敢承认现实。这个时代,知识获取方式变了,人才成长路径多元了,可我们的评价体系还在用三十年前的尺子量未来。我们不怕标准严,只怕标准脱离实际;我们不怕监管,只怕监管变成壁垒。”
他说完坐下,全场寂静十秒,随后爆发出掌声。不止一人悄悄递来写着“继续深挖案例”的纸条。
一个月后,《指导意见》正式印发,其中明确写道:“探索构建以成果产出为导向的职业能力认证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依法开展能力评估工作。”
“灯塔”被列入首批试点推荐单位名录。
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降临。
九月初,四川省人社厅突然宣布将举办“全省数字技能大赛”,优胜者可直接获得中级职称评定资格,并纳入人才引进计划。表面看是利好,细究却发现参赛门槛极高:必须持有教育部认可的职业院校结业证书,且指导教师需具备高级职称资质。
“这是冲着我们来的。”陈昊看完文件冷笑,“咱们的学员绝大多数没文凭,阿迪力这样的民间讲师更是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
林小雨咬牙:“他们想用一场‘公平竞赛’,把我们所有人挡在门外。”
江辰却笑了:“那就办一届属于普通人的比赛。”
三天之内,“灯塔”发起“草根创客挑战赛”,面向全国学员征集解决本地实际问题的技术方案。不限年龄、不限学历、不限地域,只要提交真实项目成果即可参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