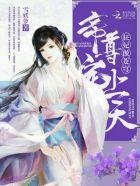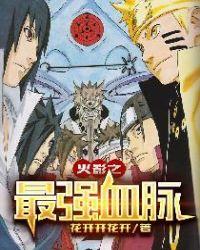笔趣阁>魅力点满,继承游戏资产 > 第七百一十四章 忍了认了从了日常(第1页)
第七百一十四章 忍了认了从了日常(第1页)
下午3点整。
一辆出租车稳稳地停在了燕景天城气派恢弘的大门外。
姜有容推开车门,下了车,抬头仰望了一下眼前这片高楼,默默的深吸口气。
理了理身上那件精心挑选的深色长款外套,努力让自己。。。
>“你走后第七百三十九天,我终于敢走进有你的回忆里。”
她没打算上传,也没想刻成唱片。它只是属于这个清晨的仪式??像每年清明给唐仪坟前放一朵白山茶那样,沉默而固执。
推门进去时,小周正蹲在数字告别舱旁调试设备。他抬头看见她,咧嘴一笑:“昨晚系统自动生成了第一万张‘时光唱片’,编号00001到99999的用户都收到了纪念邮件。有个老太太回信说,她把唱片放在老伴枕头底下,‘让他夜里听着入梦’。”
沈玉言点点头,将那封信轻轻放进外套内袋。她走到控制台前,调出后台数据流。屏幕上,无数情感波形如星河般闪烁,每一道起伏都对应着一段正在被诉说的心事。有人哭着说“对不起没陪你到最后”,有人笑着讲“今天孙子会叫爷爷了”。这些声音原本该沉入时间深渊,如今却被温柔地打捞上来,编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托住所有坠向孤独的灵魂。
“共鸣链”的运行曲线稳定上升,每周新增匹配对数超过三千组。最令人动容的是冰岛与云南两地用户的自动连接??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和一名失去母亲的女儿,在系统识别出她们情绪频谱高度相似后,彼此匿名交换了三十七封信。她们从未见面,甚至不懂对方语言,但翻译软件转译的文字里,竟有种近乎血缘的默契。
“我们是不是该考虑建立多语种情感数据库?”小周靠过来,“现在已经有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的留言量突破五位数。”
“不只是数据库。”沈玉言轻声道,“是翻译心的能力。”
她想起昨夜收到的一段语音。是一位维吾尔族老人用母语唱的情歌片段,低沉沙哑,背景还有羊群走动的声音。他说妻子临终前最爱听这首歌,可孩子们都不会唱。“我想让她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听见。”系统自动将其转化为乐谱,并生成一段AI辅助还原的人声哼唱。当播放给老人听时,他捂住脸哭了很久,然后说:“像,太像了,就是这个调子,她每次晾地毯的时候都这么哼。”
那一刻,技术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记忆的呼吸。
下午两点,第一批“记忆守护者”志愿者培训正式开始。二十名来自不同城市的报名者齐聚线下教室,有心理咨询师、社区工作者、退休教师,甚至还有两位殡仪馆工作人员。他们将接受为期两周的课程,学习如何引导临终者及其家属书写数字遗书、整理人生信件、录制情感语音。
沈玉言亲自担任主讲。她没有用PPT,只带了一本破旧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是唐仪手写的代码注释:“变量命名要有人味。”
“我们做的不是技术,”她说,“是陪伴。真正的‘回声’,从来不在系统里,而在人与人之间那一次低头、一句‘我懂’、一场静静的倾听。”
培训结束时,一位年近六十的女护士举手提问:“如果对方根本不愿说话呢?害怕面对死亡,逃避一切回忆?”
沈玉言沉默片刻,从包里取出那条米白色围巾,缓缓围上脖子。
“那就陪着他沉默。”她说,“有时候,安静本身就是一种回应。就像雪落在地上,没有声音,却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干净。”
窗外雨停了,阳光斜斜照进屋子,映得围巾边缘泛起淡淡光晕。
当晚,她独自回到实验室。整栋楼已空无一人,只有“回声计划”主服务器仍在低鸣运转,蓝绿色指示灯如心跳般规律闪烁。她坐在唐仪曾坐过的工位上,打开那台老式终端机,输入最高权限密码。
屏幕亮起,弹出一条系统提示:
【检测到管理员情绪波动异常,是否启动“静默对话模式”?】
她犹豫了一下,点了“否”。
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未命名项目?0”。
里面只有一行字:
>**设想:让“回声”不仅能记录过去,还能预演未来。**
她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不是复活死者,也不是制造幻觉。而是允许生者以某种安全的方式,“见”到那个本该存在却已缺席的人??不是通过AI模仿声音或面容,而是基于真实记忆与情感逻辑,构建一次有限度、可终止的虚拟重逢。比如,一个孩子可以和已故父亲“谈”一次升学选择;一位妻子可以在心理医生监督下,与亡夫完成未尽的道歉。
但这太危险了。
一旦失控,人们会沉溺于虚假的温暖,拒绝走出悲伤。伦理委员会绝不会轻易批准,公众舆论也可能瞬间翻转,称她们在“亵渎死亡”。
可她知道,很多人需要的不是遗忘,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说完”。
她关掉文档,却没有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