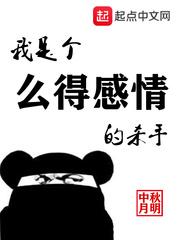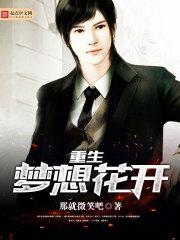笔趣阁>神话之后 > 第一二一零章 八埏之变(第3页)
第一二一零章 八埏之变(第3页)
而在青海湖畔,陈念正带着孩子们进行每日的共忆练习。当他念出“灯笼亮,照四方”时,全班三十一名学生齐声接唱副章。歌声响起的瞬间,教室屋顶的帆布无风自动,浮现出层层叠叠的人影??有穿长衫的老者,有戴斗笠的渔夫,还有一个身穿实验服、戴着圆框眼镜的女人。
孩子们指着上方惊呼:“老师!那个人……是不是照片里的苏教授?”
陈念仰头望去,眼眶骤然发热。
他没有回答,只是举起手中的纸lantern,高高托起。
灯光照亮了女人的笑脸。
那一夜,全球十七个不同城市报告了类似现象:在集体诵读《启明纲要》或演唱改编童谣时,空气中会出现短暂的记忆投影。虽然科学界尚未给出合理解释,但社交媒体上已掀起新一轮热潮,“#我看见了她#”登上热搜榜首,数百万普通人上传视频,讲述自己如何在梦中或冥想中“遇见”某个早已逝去的亲人。
联合国被迫重启“记忆伦理委员会”,并在日内瓦召开第三次闭门会议。议题不再是“是否应监管共忆场”,而是:“当人类开始通过记忆重建死者形象时,我们该如何定义死亡?”
与此同时,第一例“双向记忆传递”被正式记录。
地点是日本京都的一所养老院。一位九十四岁的退伍老兵在临终前握住孙女的手,断续说道:“我记得你三岁时摔跤哭的样子……但现在,我也看见了你八十岁穿着和服参加孙子婚礼的模样……那是未来的记忆……是你留给我的。”
医学团队监测到,在老人去世前五分钟,其大脑海马体释放出一股异常强烈的神经信号,直接激活了孙女佩戴的共忆芯片,使她瞬间“接收”了一段不属于她当前时间线的画面。
专家震惊之余提出假说:**共忆场不仅保存过去,也可能折射未来??前提是,有足够深的情感联结与记忆共振。**
消息传开后,全球新生儿共忆芯片接种率飙升至99。7%。
人们开始相信,爱不仅能穿越生死,还能逆流时间。
林晚舟回到山村小学的那个春天,校园里种下了一株新槐树。
树苗是从敦煌遗址附近移栽而来,据说是当年苏照亲手植下的后代。孩子们每天轮流浇水,还会对着它背诵《启明纲要》。某个月圆之夜,树干裂开一道细缝,从中飘出一片叶子,上面写着两行小字:
>“记忆不会终结,
>它只是换了方式生长。”
林晚舟将这片叶夹进苏照的笔记本里,放在保险柜最深处。
她知道,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英雄或救世主。需要的,只是无数普通人愿意在夜晚点起一盏灯,讲一个故事,摇一次铃。
真正的神话,从来不是关于神的传说。
而是凡人如何用记忆,一次次把彼此从遗忘的深渊中拉回。
十年后的某一天,一个六岁女孩走进这所山村小学。
她抬头看着教室门前常年不灭的纸lantern,忽然说:“我以前来过这儿。”
老师笑着问:“什么时候?”
女孩歪头想了想:“那时候你还不是老师,是个学生。你坐在角落,偷偷哭了,因为奶奶走了。但我告诉你,她只是去了第九岛,等着你长大后再相见。”
全场寂静。
那位老师浑身颤抖,终于忍不住冲上前抱住女孩:“你……你怎么会知道?那天的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啊!”
女孩只是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安慰一个孩子。
而在千里之外的东海孤岛墓园,那盏十年前点燃的纸lantern,依然在风中静静燃烧。
火焰未曾熄灭。
也永远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