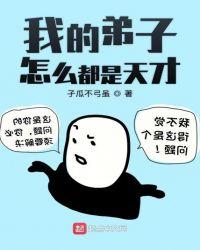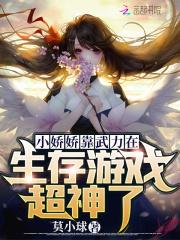笔趣阁>从机械猎人开始 > 第九十四章 不死领袖生物侧(第2页)
第九十四章 不死领袖生物侧(第2页)
音乐再次响起。
这一次,他跟着哼了起来。声音干涩、走调,甚至带着愤怒的咬牙切齿,但每一个音符都真实无比。渐渐地,其他人也开始加入。有人唱起了童年儿歌,有人念出逝去亲人名字,还有人只是反复说着“对不起”“谢谢”“我想你了”。
那一夜,失语谷第一次有了声音的河流。
它不汹涌,却绵长;不完美,却自由。
七天后,第一座由本地居民自发建造的“共鸣亭”落成。材料是回收的金属板和压电纤维,外形粗糙,却能在风雨中自动调节声场,将人们的话语转化为柔和的光晕投射天空。消息传开后,周边几个被遗忘的城镇陆续派人前来学习技术。他们不要施舍,只要方法。
林远离开时,阿哲追出来,塞给他一张手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一首他自己编的歌词:
>“我不是英雄,也不是罪人,
>我只是一个想被听见的普通人。
>若有一天世界再次忘记我们,
>请让这首歌,替我说出我的存在。”
林远将纸条折好,放入贴身口袋。他知道,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心声,而是千万个曾被边缘化灵魂的共同宣言。
旅途继续。
两年后,他在南太平洋一个小岛上遭遇极端组织“理性之刃”的伏击。这群人坚信情感共鸣是精神污染,主张回归纯粹逻辑社会,已炸毁三座声构建筑。他们用屏蔽场封锁岛屿,切断所有外部通讯,企图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处决林远。
审讯室内,首领戴着眼镜,语气冷静得近乎残酷:“你传播的不是和平,是依赖。人类不该靠‘感觉’活着,而应依靠数据与理性。”
林远坐在铁椅上,手腕被电磁锁扣住,却神情平静:“你说得对。单靠感觉,确实无法造桥、治病或预测天气。但告诉我??当你母亲去世时,你是用哪组公式来处理内心的空洞?”
对方沉默。
“你们害怕的不是声音,”林远缓缓道,“是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那会让你承认:你也孤独,你也后悔,你也渴望被爱。”
话音未落,整座建筑突然震动。不是爆炸,而是来自地底的共振。原来岛民早已偷偷接入残留声网,在外围搭建了简易谐振阵列。他们不懂高深理论,只知道“那个人教会我们唱歌”。
一道由百人合唱组成的声波穿透屏蔽层,精准击溃控制系统。门开了,不是武力突破,而是看守者主动解除了枷锁。其中一人摘下帽子,露出额头上淡淡的光痕??那是早期接受过生物膜植入的痕迹。
“我女儿……”他声音哽咽,“她植物人三年,昨天醒了。她说,她一直听得见我每天给她唱的摇篮曲。”
林远没有多言,只是对他点了点头。
离开前,他在海滩上留下一段录音,埋入沙中,标注为:“致未来的怀疑者”。
内容只有两句话:
“如果你不信声音能改变世界,
那就先试着对自己说一句真话。”
五年过去了。
地球进入了“声纪元Ⅱ阶段”。全球87%人口定期参与“共感仪式”,即通过特定频率共享一段集体记忆或情绪体验。联合国改组为“谐律议会”,决策机制引入“情感权重算法”,战争基本绝迹,但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有人滥用声能操控他人情绪,被称为“伪音师”;
有企业开发“情绪定制服务”,让人付费购买虚假幸福感;
更有国家试图垄断“母语密钥”衍生技术,打造“超级共鸣武器”。
莉娜的身影再度出现,不是实体,而是通过十三位显性音种的联合共振投影于全球夜空。她的话语简洁而锋利:
>“声音不是工具,不是武器,也不是商品。
>它是生命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