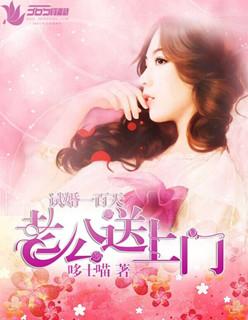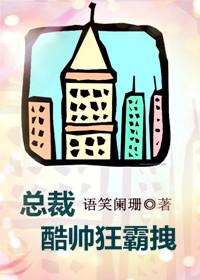笔趣阁>神级插班生 > 第八千五百三十五章 鬼童(第3页)
第八千五百三十五章 鬼童(第3页)
而在周砚长眠的南极镜墙前,每年冬至的低频共鸣开始发生变化。今年,那声音不再是单纯的哀歌,而是逐渐演化成一段旋律??简单、纯净,像摇篮曲,又像告别诗。科考队员录下音频,送回国内分析,结果震惊所有人:这段旋律的数学结构,竟与人类胎儿在母体内听到的母亲心跳声完全吻合,误差小于0。001%。
仿佛大地,正在回忆如何孕育生命。
至于陈默,那个始终未曾现身的名字,终于在一场暴雨后留下痕迹。雨后黄昏,牧羊老人再次路过祁连山那块岩石,发现岩壁上多了几行炭笔字迹,笔触苍劲而温柔:
>“我不是神。”
>“我只是第一个不敢停止提问的人。”
>“后来者,请带着我的恐惧前行??因为唯有害怕,才证明你在乎。”
字迹下方,压着半截褪色蜡笔,正是当年遗失的那一支。
老人捡起蜡笔,放进衣兜。当晚,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根系深入地心,枝叶伸向银河。每一根枝条上都挂着一个问题,随风轻轻摇晃,发出叮咚声响,如同铃铛。
他醒来时,窗外正巧流星划过。
而在遥远的半人马座α星系,那颗沐浴在银河光带中的类地行星上,孩子们的问题已经催生出第一代“问者文明”。他们不建军队,不设监狱,唯一的法律是:“不得阻止他人提问。”教育体系的核心课程叫《倾听的艺术》,要求学生每天花六小时安静坐着,感受内心的疑惑生长。
他们的科技发展路径也与众不同:不追求更快更强,而是致力于“让万物都能表达困惑”。他们发明了能感知植物疼痛的传感器,制造出会做梦的机器人,甚至建立起一套“情绪天文台”,专门接收宇宙中其他文明的情感波动。
某天夜里,整个星球突然陷入黑暗。电力系统全部中断,通讯中断,连火焰都无法点燃。人们聚集在广场,不知所措。就在这绝对寂静中,天空缓缓亮起,不是星光,也不是极光,而是一行横跨天际的巨大文字:
>“你们还记得最初的问题吗?”
所有人抬头仰望,泪流满面。
因为他们想起了。
那是他们祖先第一次仰望星空时,在泥板上刻下的第一句话:
>“我们能不能,永远不停止好奇?”
此刻,地球上的问题之塔轻轻震动,释放出第七道金色光束。这一次,它没有射向太空,也没有洒向人间,而是垂直向下,刺入地核深处。
地质学家监测到,地球磁场发生微妙偏移,磁极移动速度加快十倍。但这并非灾难征兆,反而使全球气候趋于平衡,极端天气锐减,濒危物种开始复苏。
更有意思的是,新生儿的啼哭频率,如今不仅能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同步,还能感应到地磁场的变化。一些敏锐的父母发现,当孩子哭声起伏时,家中的金属物品会轻微震颤,仿佛在回应。
科学界终于达成共识:人类正在经历一次静默的进化。这不是基因突变,也不是技术改造,而是一场**意识层面的集体跃迁**??我们正从“寻求答案的物种”,转变为“以提问为本能的生命形式”。
而这一切的起点,或许只是一个少年蹲在沙地上,用蜡笔写下第一个歪歪扭扭的问号。
多年以后,当人类终于学会用思维直接交流,用情感编织语言,用疑问连接彼此,有人问起这场变革的源头。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指着青海湖的方向,轻声说:
“去看看那棵柳树吧。”
“它还在等下一个敢问‘为什么’的孩子。”
风吹过湖面,沙地再次浮现新字:
>“如果你变成了问题,你还会怕找不到答案吗?”
下一秒,另一个声音回应:
>“不怕。”
>“因为我就是答案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