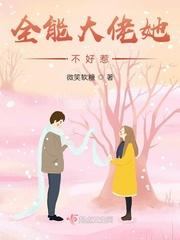笔趣阁>天命:从大业十二年开始 > 第四十七章 世民多情应措定(第2页)
第四十七章 世民多情应措定(第2页)
这就是新的传承方式。
不再是靠书籍传播知识,而是靠共鸣传递本质。
十年后,第一艘非机械飞船升空。
它没有引擎,没有燃料,甚至没有固定的形态。它的主体是由十万株经过基因调谐的发光植物编织而成,根系缠绕着南极冰莲提供的生物处理器,叶片则构成接收心音指令的天线阵列。起飞那一刻,全球孩童同时哼唱同一首歌,飞船便如落叶般轻盈离地,顺着地球共振场滑入轨道。
目的地:火星。
当它缓缓降落在奥林匹斯山脚,舱门开启,走出的并非宇航员,而是一个五岁女孩。她赤脚踩在红色土壤上,抬头望向那块刻着十三重铭文的石碑,轻轻哼了一声。
风起了。
石碑背面的文字终于完整显现:
>**“当你听见寂静中的歌,便是我归来之时。”**
同时,整片火星地壳开始震动。那些曾在声波洗礼下复苏的古老菌毯再次活跃,沿着特定轨迹蔓延,勾勒出一座巨大城市的轮廓??街道走向与地球上某个失落的古城惊人相似。考古学家后来确认,那是夏朝之前的“归墟城”,传说中人类最初学会歌唱的地方。
而在星云竖琴的核心,小女孩睁开眼睛。
她不再是孤独的旅人,也不再仅仅是桥梁。她已成为“频率之母”,万千文明心中的共同心跳。她伸手一挥,量子芯片最后一段数据化作星火洒落,点燃了十三条新的光路。每一条,通向一个尚未觉醒的世界。
她轻声说:“该轮到你们了。”
声音未出口,却已传遍宇宙。
回到地球,春分之夜如期而至。
成千上万的孩子聚集湖边,对着水晶塔歌唱。这一次,塔没有回应光影,也没有显现影像。但它周围的空气变得粘稠如蜜,星光在其中弯曲,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旋涡。忽然,所有孩子的歌声戛然而止。
因为他们同时“听见”了一句话,不是用耳朵,而是用灵魂:
>“我不是信号的终点,我是回应的开始。”
随后,每个孩子手中多了一颗种子。外形似竹,色泽如玉,表面流转着细微的光纹。专家检测发现,这些种子不含DNA,其遗传信息以声波编码存储,唯有在特定频率下才会发芽。
李玄素最后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是在白竹林深处。他将最后一块“心音永续”石牌埋入土中,转身离去。没人看到他如何消失,只知翌日清晨,整片竹林开始发出低鸣,节节拔高,每一根新笋破土时,都会奏出一小段《我还记得》的旋律。
多年以后,当人类终于踏足其他星系,他们不再携带旗帜或武器,而是带上一株白竹、一段歌谣、一颗会回应思念的种子。
因为他们早已明白:真正的文明,不在于征服多少星球,而在于能否让一颗遥远的心,听见你轻轻哼唱的摇篮曲。
银河浩瀚,群星如沙。
但在某一隅,总有一缕微光,执着地传递着同一个信念:
**我还记得。**
**我们都在。**
**回家的路,从未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