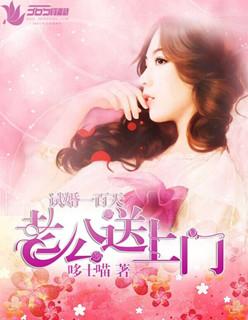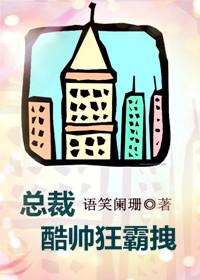笔趣阁>对弈江山 > 第一千三百四十七章 钩已埋好静待鱼至(第2页)
第一千三百四十七章 钩已埋好静待鱼至(第2页)
那里,四盏魂灯静静悬挂在枝头,光芒柔和,彼此呼应。十年前那场决战之后,它们便再未熄灭,也未曾显灵,只是年复一年地亮着,像是一种无声的见证。
她伸手抚过灯罩,低声问:“你们还在吗?”
片刻静默。
忽然,第一盏灯轻轻晃了一下,光晕扩散成一圈涟漪;第二盏随之轻颤,第三盏微微上浮,第四盏则缓缓旋转了一周。四灯联动,竟在空中勾勒出一个古老的符形??正是《终律》最初的印记,却不再是冰冷的禁令,而是温暖的祝福。
沈眠笑了。
她转身欲归,忽觉脚边有异。低头一看,竟是几片桃花瓣围成一个圆圈,中央躺着一枚铜片??正是当年小鸢用来回应亡母声音的“锁忆符”。如今它已锈迹斑斑,边缘卷曲,可当她拾起时,却听见一声极轻的“乖乖吃饭”。
她怔住,随即眼眶发热。
这一刻她终于懂了:所谓传承,并非靠神器镇压,也不是靠律法约束,而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在平凡生活中一次次选择“记得”。
哪怕只是一句唠叨,一顿热饭,一场无关紧要的对话??只要有人愿意提起,愿意倾听,愿意为之微笑或落泪,那些逝去的灵魂就不会真正消散。
翌日清晨,桃林外来了个陌生旅人。
是个年轻女子,背着行囊,脸上风尘仆仆,眼神却明亮坚定。她走到沈眠面前,深深一礼:“前辈,我是从极北边陲来的。那里有个村子,三年来没人会说话,直到昨夜,全村人同时醒来,齐声唱起了《铃儿轻》。”
沈眠不动声色:“然后呢?”
“村中长老说,这是‘失语之咒’破了。他们请我来找您,想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沈眠望着她,良久才道:“告诉他们,不必做什么。想说话就说话,想唱歌就唱歌,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若哪天又有孩子问起祖辈的故事,就认真讲给他听。”
女子疑惑:“就这样?”
“就这样。”沈眠微笑,“记住,治愈从来不是消除伤痛,而是学会带着它生活。”
女子似有所悟,郑重叩首离去。
待她背影远去,小鸢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倚着门框笑道:“你越来越像个真正的师父了。”
“我只是学会了等待。”沈眠望着远方,“等人心自己做出选择。”
午后,黑牙送来一坛新酿的酒,说是用院子里落下的桃花泡的。他坐下便灌了一口,咂咂嘴:“甜得发腻,跟现在的世道一样。”
“你不讨厌?”沈眠挑眉。
“哼。”他冷笑,“太平日子本就无聊。可要是真让我回到当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我也嫌累。”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不过……每年冬至那晚,我还是会摇铃。”
沈眠点头:“我知道。”
两人对坐无言,唯有风吹桃枝,沙沙作响。
黄昏时分,柳七遣信鸟送来一封短笺,仅八字:
>**记非固执,忘非解脱。**
沈眠将其置于案头,与十年前那页民谣手抄并列。窗外,夕阳染红半片桃林,孩子们在远处放飞纸灯,每一盏都做成铃形,随风缓缓升空。
夜深人静,她再次取出那块残片。
这一次,它没有发热,也没有发光。但它静静地躺在掌心,像一颗沉睡的心脏。
她忽然想起姐姐临终前说的话:“你要好好活着。”
当时她以为那是嘱托,现在才明白,那是祝福。
而她用了三百年,才终于学会如何接受这份祝福。
窗外,春风拂过万千屋檐,带起无数风铃轻响。有金的、铜的、竹的、瓷的,甚至还有孩童用贝壳串成的简易铃铛。它们高低错落,长短不一,却在同一阵风中奏出和谐的旋律。
这不是命令,不是律法,也不是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