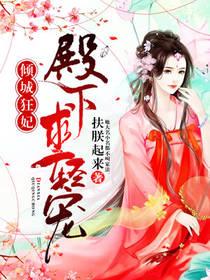笔趣阁>对弈江山 > 第一千三百四十八章 八嘎现身(第3页)
第一千三百四十八章 八嘎现身(第3页)
与此同时,北方边陲的小村里,那个曾三年失语的老者突然睁开了眼。他颤巍巍站起身,走到屋外晒谷场上,仰头望着蓝天白云,张开嘴,发出沙哑却坚定的第一个音节:
“啊??”
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接连响起。全村人仿佛被唤醒,纷纷走出家门,互相拥抱、哭泣、呼唤彼此的名字。有人拿起锅铲敲打铁盆,有人吹响多年未碰的竹笛,有人干脆放声高歌??歌词早已模糊,旋律支离破碎,但他们不在乎。
因为他们终于又能说话了。
而在极南海岛的一间老屋里,一位盲眼婆婆忽然伸手摸向床头柜,准确抓住了一张泛黄照片。她虽看不见,却笑着说:“是你爸年轻时候的样子吧?我记得他最爱穿那件蓝布衫……他还活着吗?”
她的孙女泪流满面,紧紧抱住她:“奶奶,他已经走了三十年了……可是您一直记得他,所以他从来没真正离开过。”
同一时刻,西域沙漠驿站中,一名旅人翻检祖辈遗物,意外发现一封未曾开启的信。信封上写着:“致吾妻,若此生不得相见,请于每年清明读此书。”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页空白纸,但在阳光斜照之下,隐约显现出一行极淡的字迹:
>“我始终相信你会来接我。”
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但所有人都感觉到,心里某些长久压抑的情绪,正在悄然融化。愤怒变得柔软,悲伤有了出口,孤独找到了回音。人们开始主动提起那些尘封的往事,不再害怕流泪,也不再羞于表达爱意。
一年后,第一所“忆学堂”在京城建成。
不是教授权谋兵法,也不是研习经史子集,而是专门讲授如何记住一个人??如何保存一段对话,如何转述一个故事,如何让孩子懂得祖辈的艰辛与温柔。课堂上没有考试,唯一的作业是:每周回家,问长辈一个问题,关于他们小时候的事。
十年之内,这样的学堂遍布全国。
又过了二十年,孩子们课本里多了一篇名为《铃与风》的文章,作者署名为空白。文中写道:
>“世上本无永恒之物,唯有记忆能让刹那成为永远。当你想起一个人的笑容,那一刻的光便重新照亮你的世界。铃声之所以不绝,并非因为它从未破碎,而是因为总有那么一些人,愿意在风起之时,轻轻说一句:我还记得。”
沈眠活到了第一百零八岁。
没有人亲眼见过她衰老的过程,就像没人说得清她是何时来到桃林的。某年春天,她像往常一样坐在院中喝茶,忽然对前来探望的小鸢说:“我想睡一会儿。”
小鸢应了一声,转身去厨房煮粥。等她端着热腾腾的米汤回来时,椅子上只剩下一袭空衣,茶杯尚温,窗台上那枚泥铃静静立着,表面浮现出一圈细微裂纹,随即化作粉末,随风而去。
但从那天起,每逢春暖花开,桃林深处总会传出若有若无的歌声。
樵夫说听过,牧童说听过,就连路过的商旅也说,在夜宿林间时,听见有人轻轻哼唱:
>“铃儿轻,心儿定,
>不怕黑夜长,只因有人等……”
人们不再寻找声音的来源。
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人在离去之后,反而更加无处不在。
很多年后,有个小女孩在放学路上捡到一枚铜片,锈迹斑斑,却隐约可见一朵小红花绣纹。她不懂来历,拿回家给奶奶看。老人接过一看,老泪纵横,颤抖着从箱底取出一双破旧布鞋,正好缺了鞋尖那朵花。
“乖乖,”她抱着孙女轻声说,“这是曾外婆留给我们的。她说,只要还记得她做的鞋,她就能听见我们说话。”
小女孩眨眨眼:“那我现在告诉她,今天我学会写字啦!”
老人笑着点头,抬头望向窗外。
春风拂过屋檐,无数风铃齐鸣,高低错落,长短相和,奏出一曲不属于任何时代的乐章。
那不是命令,不是警告,也不是哀悼。
那是生活本身,在岁月长河中轻轻吟唱。
铃声响起之处,即是归途。
而每一个愿意说“我记得”的人,都是这漫长旅途上的守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