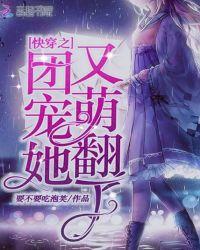笔趣阁>逍遥四公子 > 第1936章 口不择言(第1页)
第1936章 口不择言(第1页)
翌日,上午巳时!
北城衙门堂外挤满了百姓。
卫鹰,路勇,还有穆安邦这个证人,准时到了。
但梁世昌还没到。
直到巳时快过的时候,外面开路的锣声响起。
梁世昌排场很大,姗姗来迟。
同行的还有总府的闻师爷。
两人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公堂之上,看向黄梓谦的眼神里满是冷笑。
梁世昌扫了一眼卫鹰几人。
后者也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春风拂过西域荒原,卷起黄沙如雾。那青年坐在客栈门槛上,手中剑已擦拭了整整三日,锈迹渐褪,露出一线青光,像是沉眠多年的魂魄终于睁开了眼。他名叫林隐,本是无名孤儿,自幼被一位游方道士收养于戈壁深处。十岁那年,道人临终前将这把剑与铜铃交到他手中,只留下一句话:“若你听见铃声响起,便是归途开始。”
那时他不懂何为归途,也不知自己从何而来。
直到昨夜,风停沙静,铜铃忽鸣??不是风吹,而是自响。那一瞬,他脑中炸开无数画面:雪峰之巅的塔影、断桥边的伞下女子、一场大火吞噬整座山谷,又有一少年在冰窟中苏醒,手握半枚残铃……最后定格在一个名字上??**沈砚**。
他跪倒在地,冷汗浸透衣衫。
“这不是梦。”他喃喃,“这是记忆。”
他不知道是谁的记忆,也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自己识海之中,但他明白,这一程,非走不可。
晨光初露时,林隐背上长剑,推门而出。客栈老板追出来喊:“客官,你还欠三天饭钱!”
他头也不回,只从怀中抛出一块玉简。老板接住一看,竟是铭心阁传灯令残片,上面浮着一行小字:“持此令者,天下皆通。”
那是去年一名路过的传灯人留下的信物,据说凡助人破心魔者,便可得一片。而眼前这青年,竟随手便掷出如此重宝。
“疯子!”老板骂了一句,却忽然怔住。只见远方沙丘之上,一道身影孤行而去,背影笔直如剑,腰间铜铃随步轻响,仿佛与天地同频共振。
与此同时,断桥畔的传灯亭内,苏挽晴正将最后一册《明心录》封存入匣。
这一年里,已有三千余人成为传灯人,足迹遍布九州。他们不称师、不立派,只以一盏心火照亮他人暗夜。有人用三年时间劝一个执念深重的老兵放下仇恨;有人在瘟疫村中守尸七日,只为完成亡者遗愿;更有盲女以琴声引百人共忆往昔,竟自发凝聚出微弱净火,点燃了一盏属于众生的心灯。
苏挽晴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不是靠一人之力撑起苍穹,而是让每一颗心都学会发光。
她合上匣盖,抬头望天。春雨未歇,云层厚重,可她却感到一丝异样:今日的风,带着极北的气息,冰冷而清醒,像某种古老的召唤。
“来了。”她轻声道。
陆昭匆匆步入亭中,手中捧着一面青铜古镜??正是铭心阁镇阁之宝“照心鉴”。此刻镜面波光荡漾,映出的并非亭中美景,而是一条蜿蜒向南的黄沙之路,路上有个背影,腰悬铜铃,步步生莲。
“是他。”陆昭声音发紧,“那个携带守望之铃的人,正在靠近。”
苏挽晴起身,指尖抚过镜面,低语:“不,不是‘他’。是‘它’选择了载体。就像当年金戒选我,心灯选沈砚……如今,守望之铃也在寻找它的主人。”
“您要见他吗?”
她沉默片刻,摇头:“不必。让他一路走来,看尽人间烟火,历遍悲欢离合。唯有如此,当他在断桥前停下脚步时,才能真正听懂那句‘勿忘沈砚’背后的重量。”
话音刚落,照心鉴突然嗡鸣一声,镜面碎裂成九片,每一片都浮现出不同景象:
其一,江南水乡,一名书生提笔写下家书,泪落纸面:“父病重,儿不能归,唯愿天下太平,百姓安康。”
其二,北境军营,老兵燃尽最后一缕记忆,助新兵驱散心魔,含笑而逝。
其三,西南苗寨,少女以血祭鼓,唤醒族人心中久违的勇气,对抗瘴疠之毒。
其四,东海渔村,老渔夫驾舟出海,带回溺水孩童,临终前说:“活着,就是最大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