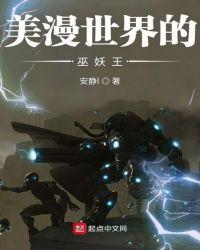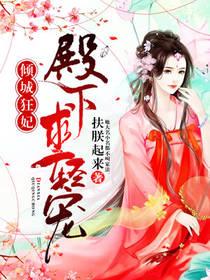笔趣阁>剑走偏锋的大明 > 第九百六十五章 拒绝和同意(第4页)
第九百六十五章 拒绝和同意(第4页)
消息传开,邻近七村纷纷效仿。地方官上报朝廷,称“民间结社成风,恐生变乱”。
此时,北京城内一场辩论正在御前展开。
大学士纪晓岚力谏:“与其严防死守,不如因势利导。可设‘实学馆’,专授算术、农政、水利、商法,既安民心,又强国本。”
保守派怒斥:“此乃纵容邪说!若准百姓自治议政,岂非动摇祖制?”
乾隆沉思良久,终允试行三县。
第一批“实学馆”挂牌那天,陈素娥已卧床不起。
孙女端来药汤,她推开,只说:“拿纸笔来。”
颤抖的手写下最后一句话:
>“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教,就还有希望。”
片刻后,含笑而逝。
出殡那日,十里八乡来了上千人。没有锣鼓,没有旌旗,人人胸前别一朵野菊花。孩子们轮流抬棺,一步一诵《女童识字歌》。当队伍经过溪边石凳时,一名盲童突然停下,大声背诵:
>“我有双眼看世界,
>我有双耳听是非……”
声音清亮,如春雷滚过原野。
三年后,云南腾冲边哨,一名年轻士兵在战壕壁上刻下新标语:
**“我们不是炮灰,是守卫家园的人。”**
旁边有人接刻:
**“陈婆婆说过:挺直腰杆站着,才能看见远方。”**
而在东海深处,苏芸率领船队重返福建沿海。此次航行不再秘密,船上悬挂一面素白旗帜,中央绣着一个大字??
**“教”**
船靠岸时,迎接他们的不再是追捕,而是数十名手持油灯的乡绅与塾师。为首者拱手道:“我们读了您们的书,想办一所‘新式义学’,请赐名。”
苏芸望向岸边晨雾中的青山,缓缓道:
**“就叫‘寸光书院’吧。”**
“何解?”
“沈文远先生遗训:不求速效,但争寸光。”
风拂海面,浪花如雪。
一艘小舟载着第一批教材驶向内陆,船头坐着一个十岁女童,怀里紧抱一本《基础公民手册》,封面已被摩挲得发亮。
她仰头问母亲:“娘,什么是‘公民’?”
母亲指着远处升起的朝阳,轻声说:
“就是从今往后,你可以堂堂正正地说??这天下,也有我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