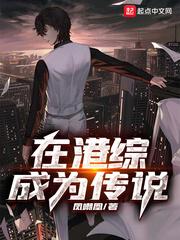笔趣阁>剑走偏锋的大明 > 第九百七十六章(第1页)
第九百七十六章(第1页)
陈循被说服了,当即拉着他去选址。
先选纺织厂的地址。
纺织厂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制造纺机和织机,一部分则是纺线织布。
布料还罢,织机和纺机却需要大运力,所以放在京城不合适。。。。
胡澄坐在工部衙门的偏厅里,手中捧着一卷泛黄的图纸,指尖轻轻摩挲着边角。窗外秋风卷起落叶,掠过青石板地,发出沙沙声响。他目光未动,思绪却早已飞出京城,落在那片尚未开建的钢铁厂地上??河北磁州,太行东麓,煤铁丰沛,水道初通,正是大明百年未有之机。
“国师。”陈循推门而入,声音压得极低,“疏要已呈御前,陛下昨夜彻读三遍,今晨召见于阁老,密议半个时辰。据说……龙颜甚悦。”
胡澄抬眼,嘴角微扬:“龙颜悦不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步踏出去,再无回头路。”
陈循坐下,袖中取出一封密函,递过去:“这是户部刚拟的预算,照你那份疏要里的条陈,头三年需银三百二十万两。季言咬牙批了八十万,余下要咱们自己筹。”
“八十万?”胡澄轻笑一声,“连个高炉都铸不成,还谈什么炼钢?”
“所以才来找你。”陈循盯着他,“你说经营,到底怎么个经营法?莫非真要学江南那些豪商,靠发卖股份集资?可这可是朝廷命脉,岂能交由民间?”
胡澄将图纸缓缓展开,指着其中一处标注:“你看这里,磁州以南六十里,有铁矿三处,储量足供百年。但若只采铁、炼铁,成本太高,百姓不愿来,匠人也不愿留。我打算以工养工??先设水泥窑、砖瓦厂、石灰坊,就地取材,就近售卖。京师营建日繁,每年光修宫殿、城墙、官廨所耗建材,便值百万两以上。这些小厂头年便可盈利,所得反哺钢铁厂。”
陈循怔住:“你是说……用民需养国器?”
“正是。”胡澄点头,“百姓要住屋,官府要修城,军队要火器,哪一样离得开建材?我们不靠国库输血,而是让工部自己造血。今日烧一窑砖,明日就能换回一口锅、一把锄,后日便可铸一尊炮。”
陈循呼吸渐重:“可这等事,须得有人管、有钱投、有章法……你一人如何兼顾?”
“所以我请了你。”胡澄直视他双眼,“陈尚书,你掌户部多年,最懂钱从何来、往何处去。我不求你拨巨款,只请你准我‘工产抵税’之策??凡参与工部各厂者,可用产出折算赋税,甚至换取盐引、茶引。如此,商贾自会趋之若鹜。”
陈循倒吸一口冷气:“这……等于是开了私贩之口!”
“不是私贩,是官督商办。”胡澄语气坚定,“工厂归工部统辖,原料由官府专营,利润三成归国库,七成用于再生产。商人只出人力与流动资金,不得染指核心技术。十年之内,所有火铳、战船、铁路所需钢铁,皆由我工部供给,绝不假手外人。”
“铁路?”陈循几乎失声。
胡澄一笑:“你还记得我在宣德年间上的《车马革新疏》吗?那时我说可用蒸汽牵引铁轨行车,日行百里不止。当时无人理会,如今时机已至。钢铁一成,铁路可兴;铁路一通,四方辐辏,粮运、兵运、商运皆可提速十倍。这才是真正的富国强兵之道。”
陈循久久无言,良久才道:“你可知此举一旦推行,天下士绅必视你为眼中钉?他们靠田租立身,你却要把农民从土地上拉走,让他们进厂做工,拿月钱吃饭。这不是动摇国本,是什么?”
“国本从来不是土地,而是人。”胡澄站起身,走到窗前,“你看外面那些挑担的、拉车的、扫街的,哪一个不是百姓?他们祖祖辈辈种地,却被地主剥去七成收成,活得不如牛马。我要给他们另一条活路??不必依附地主,不必看天吃饭,只要肯干活,就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陈循沉默许久,终于叹道:“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狠。别人改革,都是在旧壳子里添油加醋,你却是要另起炉灶。”
“旧壳子早就烂透了。”胡澄冷冷道,“你以为清丈土地就能解决问题?错了。就算把隐田全挖出来,分给贫民,不出二十年,又会被兼并殆尽。唯有工业化,才能打破这个轮回。当一个农民发现,在工厂做工比种地收入更高、更稳定,谁还会死守那一亩三分地?当地主发现雇不到人耕田,自然只能降租、改良、合作,否则就得破产。”
陈循苦笑:“所以你是借工业倒逼农业变革?”
“正是。”胡澄转身,“而且不止农业。你想过没有,一旦钢铁量产,火器便可大规模列装。现在的神机营,每人一年配发火药不过十斤,为何?因为枪管铸造不良,易炸膛。若用标准化钢材制造枪炮,不仅寿命延长,成本还能下降六成。届时,十万新式火器军可成,边防何愁不固?”
陈循心头一震:“你是想重建军制?”
“不是重建,是升级。”胡澄眼中精光闪动,“戚继光日后练兵,靠的是纪律与阵法;我今日所谋,是要让大明军队彻底进入火器时代。不再是冷热兵器混杂,而是以火器为主力,辅以机械化运输。将来,我会造出可以自行行走的铁车,载炮冲锋;造出会飞的木鸢,侦察敌情;甚至……造出能在水下航行的铁船,潜袭敌港。”
陈循听得脊背发凉:“你这是要把大明变成一座巨型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