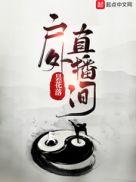笔趣阁>仙工开物 > 第419章 王命启程(第1页)
第419章 王命启程(第1页)
班积神色阴沉:“是的。最早的时候,我从皮覆劫那里得知,那宁拙拥有金丹技术的机关人偶,便想谋夺过来。”
“我便先查了一下他的情报,而后递了一封飞信,言说切磋之意。”
“哪里料到这位筑基中期的。。。
宁小满的手掌贴在锅壁上,感受着那股温润却不灼人的热意。乳白色的火焰在锅底静静燃烧,没有噼啪作响的柴火声,也没有刺鼻的烟气,只有微微震颤的光晕一圈圈扩散,像心跳,像呼吸。他闭上眼,仿佛听见了父亲的声音??不是从耳边传来,而是自心底升起,低沉、温和,带着一种久违的安稳。
“你做得很好。”那声音说。
他猛地睁开眼,四周无人。林素娥正在教一个学生切姜丝,老学者伏案书写新的传承录,学生们围坐在桌边低声交谈。可他知道,刚才那一瞬,不是幻觉。那是血脉里的回响,是火种与火种之间的对话。
“老师。”他走到老学者身边,声音很轻,“我想知道……我爹当年,是怎么开始的?”
老学者停下笔,抬头看他,目光深邃如古井。他合上笔记,缓缓起身,走向铁锅。手指轻轻抚过锅底那个“圆中一点”的印记,像是在唤醒一段沉睡的记忆。
“宁拙不是天才。”他说,“也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饿过太久的人。”
风忽然静了。院中的灯火微微摇曳,仿佛时间也屏住了呼吸。
“六十年前,地球经历第三次大断电潮,能源枯竭,城市瘫痪。粮食运输中断,超市空荡,政府配给制崩溃。那时候,人吃土、吃纸、吃皮带都不稀奇。南街七号那时还叫‘救济巷’,是城里最后一个维持供餐点的地方。每天凌晨三点,这里就开始熬粥,用最后一点存米,兑上野菜根和树皮粉。”
他顿了顿,眼神飘向远方。
“你父亲就是那时候来的。十七岁,瘦得像根竹竿,穿着一件破棉袄,脚上缠着麻绳。他不是志愿者,也不是工作人员,只是个排队等饭的少年。可有一天,轮到他领粥时,他没接碗,而是蹲下身,帮厨师淘米。没人请他,也没人命令他。他就那么干了。第二天,他又来。第三天,他开始主动去邻区收捡还能用的锅具。第四天,他在废墟里挖出一口锈死的铁锅,用砂石磨了整整一夜,直到它能重新盛水。”
宁小满听得入神,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后来,那口锅成了第一灶的雏形。”老学者继续道,“但真正点燃它的,是一场雪夜。那天零下十八度,风刮得像刀子。有个老太太倒在巷口,怀里抱着个婴儿。她已经没力气说话,嘴唇发紫。食堂只剩半碗冷粥,没人舍得热。是你父亲冲进去,把那半碗粥倒进锅里,又加水,又添柴??可柴早就烧完了。他就拆了自己的棉袄,塞进炉膛。”
“他疯了吗?”有学生忍不住问。
老学者摇头:“他说:‘人比衣服暖。火比命贵。’然后他跪在锅前,双手合十,嘴里念着一首谁都没听过的歌谣。那一刻,锅底突然裂开一道缝,乳白的流质渗出,自行燃起火焰。那火不烧物,只煮粥。那一晚,三百人喝上了热饭。而你父亲,高烧昏迷了三天。”
宁小满怔住。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从未做过饭的手,此刻却仿佛被某种古老的力量牵引着,想要伸向那口锅。
“所以……”他喃喃,“他不是因为会做饭才被选中。是因为他愿意为别人饿着。”
“正是。”林素娥不知何时站在了他身后,手中捧着那只粗瓷碗,“宁拙之所以成为‘传火者’,不是因为他懂多少菜谱,而是因为他记得饥饿的滋味。他知道一碗饭能救一条命,也能救一颗心。”
她将碗递给他:“现在,它是你的了。”
宁小满接过碗,指尖触到釉面的刹那,一股暖流顺着手臂直冲脑门。眼前景象骤然变幻??
他看见年轻的宁拙站在暴风雪中,肩扛一口铁锅;
看见火星补给站的林素娥在监控屏前落泪,因为她做的汤自己沸腾了;
看见金星轨道站的小女孩哼着童谣,而AI系统自动记录下这段音频并标注:“情感峰值触发”;
看见无数星球上的厨房同时亮起乳白火焰,炊烟穿透大气层,在宇宙中织成一张发光的网……
画面戛然而止。
他踉跄一步,被林素娥扶住。
“你看到了?”她轻声问。
他点头,喉咙发紧:“那是……灶网?”
“是记忆之链。”她说,“每一个曾为他人点火的人,都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连在一起,就成了‘我们’。不是血缘的我们,不是国籍的我们,而是‘愿彼此吃饱’的我们。”
夜更深了。院外的世界依旧喧嚣,霓虹闪烁,数据洪流奔腾不息。可在这方小院里,时间仿佛慢了下来。粥锅咕嘟作响,蒸汽升腾,在空中凝成细小的光点,如同星辰坠落人间。
忽然,锅底再次震动。
这一次,不是文字浮现,而是一段旋律自锅中传出??低缓、温柔,带着木质乐器的质感。老学者浑身一震:“这是……《炊者吟》!失传百年的灶师之歌!”
音波扩散开来,竟引动天地共鸣。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开始轻微共振,发出和声;地下管网中的水流节奏随之改变;就连天上飘过的云层,也在月光下显现出波纹状的轨迹。
宁小满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他从未学过这首歌,可歌词却自然涌上舌尖:
>“一瓢水,洗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