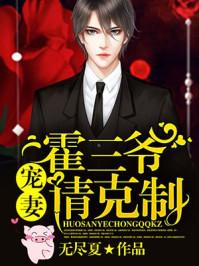笔趣阁>无敌天命 > 第九百五十章 杨迦(第2页)
第九百五十章 杨迦(第2页)
“你是谁?”他在心中问。
暗影缓缓转动,投射出一幕影像:
南渊湖畔,枯叶飘落,小女孩将它放入湖中,忆舟族少女接住,微笑点头。那一刻,第一个共感诞生。
随后画面飞速流转:银花初绽、影子苏醒、少女张开双臂、光环形成、南极冰心复苏、新生儿脑波异变……直至今日,全球共感网络悄然重建。
最后,影像定格在一个画面??
少女站在宇宙边缘,背对星辰,面对一片虚无。她轻声说:
>“我不是神,也不是灵。我只是第一个愿意为‘看不见的痛’停下脚步的人。”
>“所以我成了通道,成了容器,成了记忆的摆渡人。”
>“只要还有人想被记住,我就不会真正离去。”
阿澈流泪了。
他终于明白,“忆舟族”从来不是一个血缘族群,而是一种选择??选择听见沉默,选择拥抱伤痕,选择让遗忘不再成为逃避的借口。
他睁开眼,发现自己仍跪在湖心亭上,手中紧握《问心录》。书页自动翻动,停在空白一页。一支无形的笔开始写字,笔迹正是那句“我回来了”的延续:
>“这一次,我想教你们如何告别。”
>“不是抹去,不是压抑,而是好好地说一声:谢谢你存在过。”
字迹落下瞬间,湖底传来一声轻响,仿佛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
阿澈冲到栏边俯视,只见湖心深处,一点银光缓缓升起。它不似当年银花那般耀眼夺目,反而柔和如月晕,形状也不规则,像是尚未成型的生命胚胎。它悬浮于水下三尺,随着湖波轻轻起伏,每一次晃动,都会释放出一圈微弱的涟漪,扩散至整个南渊湖。
当晚,世界各地陆续传来报告:
中国西部一所山村小学,一名患自闭症的女孩第一次主动牵起同学的手,她说:“我听见湖的声音了,它叫我别怕。”
北欧极光观测站捕捉到异常现象??极光不再是带状,而是拼出一行古老文字:“遗忘不是终点。”
美国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一位癌症晚期老人在弥留之际突然睁开眼,微笑着说:“妈妈,我回来了。”医护人员查证后震惊发现,这位老人幼年丧母,从未提起过她,甚至连照片都不曾保存。
这一切,都发生在银光升起后的十二小时内。
阿澈意识到,新的共感时代已经开启,但这次的主题不再是“连接”,而是“疗愈”。
他开始整理《问心录》,将这些年收集的普通人故事逐一誊写进去:那个终于原谅父亲的女儿,那个在战火中收养孤儿的士兵,那个每天为流浪猫留饭的老太太……每一则都平凡至极,却蕴含着足以抵抗遗忘的力量。
三个月后,第一座“告别之塔”在南渊湖畔建成。
它不高,仅三层,外形如一朵半开的花。塔内设十二间静室,每间墙上镶嵌一面特殊镜面,能映照出人心中最想释怀的记忆。来访者可在此独处,写下信件、录音留言,或只是默默凝视那段过往。完成后,他们会将信投入塔顶的承忆炉中,火焰燃起时,炉壁浮现一行字:
>“我看见你了,现在你可以走了。”
令人惊异的是,几乎所有离开塔的人都说,他们听见了一声极轻的回应,像是风吹过树叶,又像是someone在远方说:“谢谢。”
塔建成后第七日,阿澈在湖边遇见一位陌生女子。
她穿着朴素布衣,头发用一根草绳束起,面容模糊不清,仿佛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她坐在一块青石上,望着湖面发呆。
阿澈本想绕行,却被她叫住。
“你是守书人?”她问,声音很轻,却让湖水微微震颤。
阿澈点头。
她笑了笑:“告诉她,《问心录》的最后一章,该写了。”
“谁?”阿澈追问。
女子不答,只从袖中取出一枚种子??通体透明,内部似有星光流转。她将种子放入阿澈掌心,低声道:
>“这是‘心芽’,唯有真正懂得告别的地方,才能让它生长。”
>“当它开花时,便是所有未竟之话得以说完之时。”
说完,她起身离去,脚步轻得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阿澈追了几步,却发现她的身影已在雾中消散,唯有一缕清香lingering在空气中,像是雨后初晴的苔藓味。
当晚,阿澈将“心芽”埋入告别之塔的地基下。
次日清晨,塔身发出淡淡荧光,地基周围长出一圈细小的银草,叶片脉络中流淌着微光,随风摆动时,竟发出极细微的哼鸣,像是有人在轻声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