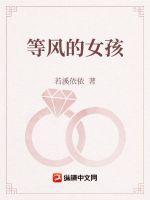笔趣阁>轮回乐园:人脉织梦师 > 第1052章 哀恸修道院(第2页)
第1052章 哀恸修道院(第2页)
“他还没说,但八九不离十。”林逸说着,后退几步,靠坐在窗边那张看起来还算结实的单人椅上,摆明了只负责后勤和压阵,将审问的舞台完全交给了咕噜。
“交给你了,问出所有情报。越详细越好。”
听到“交给你了”这几个字,咕噜的眸子瞬间亮了起来,一种近乎残忍的兴奋光芒在她眼中闪烁。
她在林逸面前吃瘪多次,憋了一肚子火气和郁闷,正愁没地方发泄。
此刻一个生命力看起来还算顽强的沙包就在眼前,简直是瞌睡遇到了枕头。
“嘿嘿,没问题~”咕噜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尖尖的小虎牙,但这笑容在她此刻的表情下显得格外瘆人,“你就瞧好吧,保证把他从小到大偷看几次女人洗澡、暗地里诅咒过几次上司都问得明明白白!就是待会儿别忘了给我刷治疗术,这家伙看起来血快流干了,不太禁玩的样子。”她说着,又用脚尖踢了踢默多克软塌塌的小腿。
林逸微微颔首:“放心,死不了。”
得到林逸的保证,咕噜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甚至可以说是明媚了,只是这明媚之下隐藏的是令人胆寒的暴戾。
她兴奋地搓了搓手,然后伸手从自己随身的储物空间里摸索起来。
只听一阵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和玻璃瓶轻响,她像变戏法一样掏出了一大堆形状各异的小玩意儿:闪着寒光的细长钩针、布满细密倒刺的精密镊子、小巧却带着血槽的骨锯、几个装着不同颜色诡异液体的玻璃瓶、甚至还有一包特制的盐和一小罐嗡嗡作响的怪异甲虫。
瘫倒在地的黑袍牧师似乎感知到了极致的危险,从半昏迷中挣扎着清醒了一些,看到咕噜手中那些工具,眼中瞬间被巨大的恐惧填满。
他试图挣扎,但腹部的重创让他连根手指都动不了,只能发出“嗬嗬”的漏气声。
“别怕嘛,很快的,我手艺很好的。”咕噜用最甜腻的语气说着最可怕的话,拿起那根细长的钩针,“我们先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热热身,好不好呀?第一个问题:你是谁?来自哪里?”
牧师紧闭着嘴,枯瘦的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眼神虽然被恐惧占据,却还残留着一丝顽固,他似乎还在试图凝聚某种残存的力量进行自我了断。
“啧,不乖。”咕噜撇撇嘴,手中的钩针精准地刺入了对方手臂上的一个特定穴位。
“呃啊——!!!”
一声压抑到极致却依旧凄厉无比的惨叫从牧师喉咙里迸发出来,他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如铁,眼球暴突布满血丝。
这种痛苦远超常规的肉体伤害,仿佛直接作用于神经末梢和灵魂表层。
“回答错误,或者说不回答,都是要受罚的哦。这是规矩。”咕噜慢条斯理地、甚至带着点艺术鉴赏般的神情轻轻转动着钩针,欣赏着对方身体每一丝无法控制的剧烈痉挛,“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你是谁?来自哪里?”
“……杀……了我……”牧师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那多没意思。活着才能体验到更多‘精彩’嘛。”咕噜毫不留情地拔出钩针,带出一小缕肌肉纤维。
她随手将染血的钩针在牧师袍上擦了擦,然后又拿起那把布满细密倒刺的镊子,目光开始在对方身体上游移,仿佛在挑选下一件艺术品的落笔点,“看来热身不够,得给你加点‘料’,帮你打开话匣子。”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对于这位地狱组织的审判长而言,无疑是他漫长生命中最为漫长和恐怖的地狱之旅。
咕噜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艺术般的残忍”。
她极其精通人体结构,深知如何造成最大的痛苦却避开真正的致命点,同时又巧妙结合了那些奇奇怪怪的道具和药剂。
林逸坐在窗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时不时抬手丢过去一道治疗术。
治疗术的光芒落下,牧师身上那些可怕的伤口瞬间愈合,连被咕噜切下来扔在一旁的“零件”也瞬间再生。
但肉体的完好无损,生命力的强行维系,恰恰使得那循环往复的痛苦可以无限重复地施加在那饱受摧残的意识之上。
每一次治疗,都意味着新一轮酷刑的开始,绝望的深渊被一次次掘得更深。
惨叫声从一开始的凄厉,逐渐变得嘶哑、微弱,最后只剩下无意识的抽搐和嗬嗬声。
咕噜玩得兴起,几乎忘了审问的初衷,完全沉浸在自己“精湛技艺”的展示中,直到林逸中间冷声插嘴,提醒并追问了几个关键问题,才勉强将几乎滑向纯粹虐杀的话题拉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