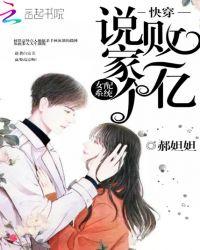笔趣阁>皇叔借点功德,王妃把符画猛了 > 第1677章 吵起来了(第3页)
第1677章 吵起来了(第3页)
这首歌没有任何高深技法,却自带一种无法抗拒的感染力。每一个字都像种子落入泥土,在听者心中悄然生根。钟体内的黑暗迅速退去,紫色光球重新净化为澄澈金芒,且比以往更加明亮。
终于,钟顶龙口缓缓张开。
那根曾象征皇权压制的音槌,竟自行断裂坠落,在触及地面瞬间化为齑粉。
取而代之的,是一道纤细身影自钟腹缓步走出??沈清璃。
她已非血肉之躯,周身萦绕淡淡音辉,每走一步,脚下便绽放一朵由声波凝成的莲花。她的右耳,聆真珠依旧闪烁,但颜色已由晶莹转为暖金色,仿佛吸纳了千万人的真心话语。
葵儿扑上前抱住她,泣不成声。
“你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
沈清璃轻轻抚摸她的发,微笑道:“我没有走,我只是学会了如何真正活着。”
老妇人望着她们,久久无言,最终只化作一声长叹:“从此以后,世上再无‘终焉钟’,唯有‘启音钟’永驻人心。帝王不能再靠声音统治,因为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钟楼。”
她抬头看向洞口,天边已有微光透出。
“该回去了。”
***
三个月后,春回大地。
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奇异现象:某些废弃寺庙的铜钟会在清晨自行鸣响,音色清越,不带半分压迫;私塾学堂里的孩童不再背诵官方教材,而是自发编写新课文,讲述祖辈遭遇的冤屈;甚至连宫中太监也开始偷偷传阅手抄本,记录前朝真相。
皇帝暴怒,下令销毁一切“异音载体”,可越是封锁,民间声音越盛。更有甚者,有人仿照启音钟原理,打造小型共鸣器,藏于井底、墙缝、树洞之中,专收普通人日常言语,夜间自动播放,称之为“夜语匣”。
而最令人震撼的,是一群盲眼乐师组成的巡游队伍。他们自称“听真社”,行走于城乡之间,采集百姓心声,编成曲目公开演奏。每当他们奏响,无论贵贱,皆驻足聆听,泪流满面。
至于沈清璃,据传她并未留在人间。
有人说她在某个月圆之夜乘风而去,身影融入一片晨雾;也有人说她化作了某座小镇祠堂檐角悬挂的小铃铛,每逢风起,便叮咚作响,提醒世人勿忘言之尊严。
唯有葵儿知其去向。
她在江南一处偏僻山村定居下来,屋前种桃,屋后养鸡,每日黄昏都会对着一口古井吹奏骨笛。井水清澈见底,偶尔泛起涟漪,倒影中会出现沈清璃的模样,对她微笑点头。
一日,村中顽童问她:“婆婆,你天天吹这个破笛子,到底在等谁呀?”
葵儿停下笛声,望向远方青山,轻声道:
“我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停下的声音。”
孩子不解。
她笑了笑,重新吹起招魂调。
笛声悠扬,穿林渡水,惊起一群飞鸟。
其中一只白羽雀儿掠过山顶,飞向北方。
它不知疲倦,一路北上,直到抵达昔日紫宸殿遗址。
那里杂草丛生,唯有一块青石静静卧于土中,上面刻字已被风雨磨平大半,只剩最后一句依稀可辨:
>“**宁为自由语,不做太平奴。**”
白雀落下,歪头看了看,忽然张嘴,清脆鸣叫了一声。
那声音不大,却仿佛敲响了某种无形之钟。
远处山坡上,一名采药少年抬起头,怔怔听着。
片刻后,他掏出随身小本,在空白页写下一句话:
>“原来,我们一直都可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