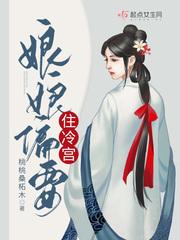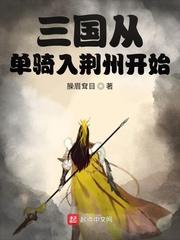笔趣阁>皇叔借点功德,王妃把符画猛了 > 第1682章 嫁出去了(第1页)
第1682章 嫁出去了(第1页)
周时阅走到殷长行他们面前,对着他们很恭敬地鞠躬行了一礼。
他认真地说,“师傅师叔,师弟师妹们,我来迎娶阿菱了,你们放心把她交给我吧。”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待阿菱的,不会伤她的心,不会让她苦恼,一切以她为先,以她为重。”
“皇室种种规矩,只要阿菱觉得不舒服,她都可以不用遵守,晋王府里,王妃便是最大的主子,那里就是她的家。也是你们的家,你们都是我的家人。”
“师父,把阿菱交给我,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岭南疫事平息之后,阿禾并未久留。他将《岭南疫录》交由直言院存档,并亲自在辩言会上宣讲三日,直至百姓心中疑云尽散,才悄然离去。临行前,柳芸送他至村口,手中捧着一株白花??那是她在废墟中救活的唯一一棵药草,名为“醒心兰”,传说是沈清璃当年南巡时亲手所植。
“它不开则已,一开便是清明。”柳芸轻声道,“就像真话,沉默多年,终有破土之日。”
阿禾接过花枝,插于行囊侧袋,点头不语。他知道,这世上最锋利的武器,从来不是刀剑,也不是诏令,而是某个人在黑暗中忽然开口的那一声。
此后十年,风起云涌,人心如潮。新政初立,百废待兴,可旧势未死,新弊又生。有些地方官借“言旅”之名敛财设卡,称凡欲进直言院者须先缴“陈情银”;有些豪绅暗中豢养笔客,伪造民间呼声,以“民意”之名行操控之实;更有甚者,竟有人冒充沈清璃遗族,四处收香火钱,建“清璃祠”,宣称只要焚香祷告,便能得“启音钟庇佑”。
阿禾一路行走,眼见这些乱象滋生,心中悲凉更胜当年。他曾在一个小镇亲眼目睹一场“真言祭”沦为闹剧:台上一名老儒生声泪俱下控诉税重民苦,台下百姓动容落泪,可当夜阿禾潜入后台,却发现那老者正数着银子笑骂:“今日演得好,明日再换一村哭去!”
他没有揭穿,只是默默记下姓名,收入《新言录?伪篇》。
回到宿处,他在灯下翻开那本已泛黄的空白册子,提笔写下:
>“言语一旦成为表演,便不再属于灵魂。
>当万人齐呼‘我说,故我在’时,
>要警惕那声音是否出自同一张嘴,同一只手牵动的线。
>真话不怕孤寂,怕的是被簇拥成假象。”
写罢掷笔,长叹良久。
次日清晨,他召集当地言社成员,在城东破庙设坛,不做宣讲,只放一张桌、一盏灯、一支笔,贴出告示:“今夜子时,愿说真话者,请独自前来,不记名,不留声,只写一字??你最不敢说出口的话。”
起初无人敢来。直到三更天,一个颤抖的身影推门而入,是个年轻妇人,衣衫褴褛,脸上带着淤青。她跪在地上,抓起笔,在纸上用力写下两个字:“他……打我。”然后伏地痛哭,跑出门外,消失在夜色中。
五日后,同样的位置,又来了个老人,写的是:“儿子死了,官府说他是暴病,可我知道,他是因说了句‘粮仓空了’被抓走的。”
再后来,有个书童模样的少年,写了:“先生教我们背《圣训》,却私下说皇帝是昏君,我该信哪一个?”
每夜一人,或两人,不多不少。阿禾从不追问,也不公开内容,只是将纸条收好,封入陶罐,埋于庙后槐树之下。他对众人说:“这些话不必让天下听见,只要它们曾被人写出,就够了。因为沉默的敌人,从来不是遗忘,而是假装听见。”
这一举动渐渐传开,各地效仿,“静言坛”由此兴起??不喧哗,不集会,只守一方净地,容一人独语。有人说这是退步,是恐惧复归;也有人说,这才是言语真正的起点:不是为了被掌声包围,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心跳。
而阿禾依旧前行。
六十岁那年冬天,他病倒在江南一座小城。高烧不退,梦中常现沈清璃身影。她站在启音钟残骸之上,披着月光织就的袍子,望着他说:“你还记得那个被锁住声音的女孩吗?”
他猛然惊醒,冷汗浸透衣襟。
原来早在三十年前,他曾途经北境边陲,遇见一名哑女,名叫阿满。那时她十二岁,双目清明,却从未开口。据村民说,她出生时天降异象,接生婆见其唇色如朱砂,惊呼“此女必乱朝纲”,遂被族长下令灌药致哑,关在地窖十年,每日仅以手势与外界沟通。
阿禾救出她时,她已形销骨立。但他记得,她第一次见到阳光时,仰头望着天空,久久不动,眼里有泪,却没有声音。
他送她一支紫毫笔,断锋的,是他从沈清璃遗物中寻得的。“若不能言,便以笔代舌。”他说。
阿满接过笔,颤抖着在地上划出第一道痕迹??是一个“人”字。
此后三年,她随阿禾同行,用笔记录所见所闻,字迹清秀如柳叶拂水。她写下农妇卖儿换粮的哀告,写下县令私吞赈灾款的账目,甚至悄悄临摹过音律监密探的脸谱。她的文字没有愤怒,却比怒吼更令人战栗。
可就在《禁语律》废除前夕,她在一次传递密信途中被捕。最后被人发现时,躺在雪地中,双手冻僵仍紧握一支断笔,胸口压着一页血书,上面写着:“我不是哑巴,我只是不说你们想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