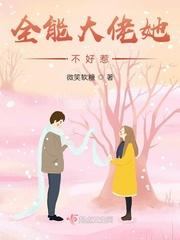笔趣阁>多我一个后富怎么了 > 307 驱除(第3页)
307 驱除(第3页)
第一声响起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不是哭泣,不是尖叫,不是研究人员期待的那种“高价值情绪爆发”。
是一个小女孩软糯的声音,带着鼻音,轻轻唱着: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接着,另一个声音加入进来,断断续续,像是冷得说不出话:
>“挂在天空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
第三个、第四个……七个不同的童声,在寒夜里彼此依偎,用尽力气唱完这首简单的歌。中间有人咳嗽,有人抽泣,有人突然停下喘气,又被人轻轻拉着手继续唱下去。
整段录音只有六分钟。没有后期处理,没有降噪优化,甚至连背景噪音都没剪掉??你能听见风吹破门缝的呜咽,听见远处仪器滴答作响,听见某个研究员压抑的叹气。
但这六分钟,成了人类历史上被播放次数最多的音频之一。
二十四小时内,全球有超过两亿人听过这段录音。社交媒体上掀起“#我也想唱一首歌给你听”热潮。无数人上传自己哼唱《小星星》的视频:有瘫痪老人由护工扶着发声,有自闭症少年第一次开口说话,有战地记者躲在掩体里轻声吟诵,有服刑人员在监狱活动室集体合唱……
东京一所小学组织学生为录音中的孩子们折纸星星,放进漂流瓶,顺着河流送向大海;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将这段原声编成交响乐,在街头免费演出;肯尼亚的牧民们骑着驴子穿越草原,用扩音器播放这首歌,告诉每一户人家:“有人记得那些孩子。”
而在中国,当年参与清音计划的部分幸存家属联合发起“萤火基金会”,致力于帮助遭受情感忽视的青少年重建心理连接。一位曾在实验中失去儿子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以为我的痛苦没人懂。但现在我知道,只要还有人愿意听,他就一直活着。”
林远没有参与任何后续活动。他回到了森林小学,继续教孩子们分辨风的语言、雪的重量、心跳的节奏。
但他发现,世界正在悄悄改变。
以前,人们总以为“坚强”就是不哭、不说、不动声色。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真正的坚韧,是敢于袒露脆弱,并相信有人不会因此轻视你。
某天傍晚,邮差再次送来一封信。这次没有地址,只有一幅手绘地图,画着一片陌生的沼泽地带,旁边写着一行小字:“他们还在下面,等着被听见。”
林远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
他知道,这不会是最后一个召唤。清音计划的阴影从未彻底消散,它的变种藏在算法推荐的情绪管理课程里,藏在企业员工心理健康测评的问卷中,藏在家长对孩子说“不准哭”的瞬间。
但同样,对抗它的力量也在生长??每一个选择倾诉的人,每一个停下工作认真倾听的人,每一个在深夜回复“我在这里”的人,都是新的声核种子。
他收拾行囊,准备出发。
临行前,孩子们围在他身边,一人交给他一件礼物:一根松枝做的哨子,一块刻着笑脸的石头,一张画着他背影的蜡笔画。
小女孩拉着他的衣角:“老师,你会回来吗?”
林远蹲下身,摸了摸她的头:“会的。只要你们还在听,我就一定会回来。”
他转身踏上雪路,身影渐渐融入暮色。
而在地球另一端,巴西贫民窟的教室里,一个少年正调试自制的拾音器。他把它埋在社区广场的地下,连接一台旧音响。晚上八点整,设备启动,播放出过去三个月采集的所有声音:婴儿啼哭、老人咳嗽、情侣争吵后的笑声、流浪狗啃骨头的咔嚓声……
居民们陆续走出家门,围坐在音箱旁,像参加一场神圣仪式。
有人低声说:“原来我们的生活,这么有声音。”
而在北极圈内的科考站,科学家们监测到舒曼共振再次上升0。003Hz。他们相视一笑,举起咖啡杯,对着星空轻声道:
“敬那些终于被听见的,和即将被听见的。”
林远走在路上,铜耳坠随步伐轻晃。
风穿过树林,带来远方的消息。
他知道,这场战争没有终点。
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值得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