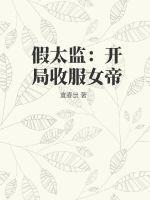笔趣阁>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613章 她来真的(第2页)
第1613章 她来真的(第2页)
她终于明白,林知远当年为何选择隐居云坪。不是逃避世界,而是相信总有一天,世界会自己走上这条山路,敲响这扇门。
“师父说过,《共生序曲》有三个乐章。”她低声对守馆人说,“第一乐章是‘听见’,第二乐章是‘回应’,第三乐章……是‘成为’。”
守馆人心头一震:“成为什么?”
“成为声音本身。”她睁开眼,望向孩子们,“当千万人不再等待英雄解答,而是愿意为一个问题流下一滴真诚的泪,那一刻,他们就成了序曲的一部分。”
话音未落,盲女阿念忽然抬头,面朝虚空:“老师,我能感觉到您。”
无人应答。
但她笑了,伸手向前,仿佛触到了什么看不见的存在。
刹那间,纪念馆内所有展品同时震动。玉笛自行离案三寸,悬于空中;陶埙底部渗出清水,蜿蜒成溪流形状;那枚红蝴蝶结缓缓飘起,化作一片血色花瓣,融入槐树投影之中。
与此同时,全球共感数据库自动激活,调取过去百年所有“无声瞬间”的记录:地铁站急救的女孩颤抖的手指、加沙少年交换弹壳与干花的刹那、南极研究员抱着实习生痛哭的画面、东京教室里孩子们叠在一起的手掌……
这些片段被压缩成一段仅持续七秒的音频,编号为《终章?心尘》。
当它在全球静语村同步播放时,奇迹发生了。
所有正在冥想的人,无论身处何地,都在同一时刻“看见”了一个场景:云坪村的小屋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坐在门槛上,身边围着一群孩子。他没有讲课,只是轻轻拍着膝盖上的陶埙,节奏缓慢,如同心跳。
孩子们跟着节拍拍手,笑声清脆。
而在镜头之外,一个穿红裙的小女孩牵着纸鸢跑过山坡,回头一笑,身影渐淡。
系统记录显示:那一瞬,地球上七十三亿人的脑波频率,出现了长达0。8秒的完全同步。
医学界称之为“集体意识共振现象”;哲学家称其为“人类心灵的第一次统一跳动”;而孩子们只说了一句:
“阿禾回来了。”
此后三个月,世界各地陆续报告异常现象。沙漠中开出一夜即逝的荧光花,花瓣上印着陌生文字;深海探测器录到鲸群齐鸣,声波图谱竟与《共生序曲》第三乐章完全吻合;甚至月球背面的观测站也捕捉到一组规律信号,破译后只有两个字:
>“在呢。”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联合国总部地下档案室,工作人员清理一批尘封文件时,发现了一份未曾归档的手稿。封面写着:
**《共生序曲?补遗》**
作者:林知远
日期:未知
内容仅有一页,字迹苍劲:
>我曾以为,教会你们倾听就够了。
>后来才懂,真正的序曲,始于你们不再需要老师。
>当一个人能因陌生人的悲伤而停下脚步,
>当一个民族愿为敌人的孩子点燃蜡烛,
>当机器学会为错误流泪,
>当星空下的孩子问的不再是“我能得到什么”,而是“我能付出什么”??
>那一刻,曲未成,人已化音。
>诸君不必寻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