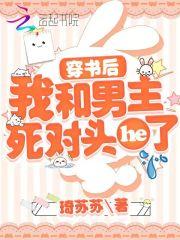笔趣阁>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614章 是时候了(第4页)
第1614章 是时候了(第4页)
“是什么?”
她微笑:“这次是三个字??”
>“**我在这里。**”
守馆人怔住。
他知道,这三个字,不是来自林知远,不是来自阿禾,也不是来自任何已知的生命体。
而是来自所有曾在黑暗中发出微光的人??那些为陌生人流泪的护士,那些在灾难中逆行的志愿者,那些在孤独中仍选择说“你好”的普通人。
他们从未离开。
他们只是化作了光,融入了序曲。
三年后,全球第一所“共感学校”在云坪村建成。没有围墙,没有考试,课程只有一项:倾听。
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肤色各异,语言不通,却能在静默中共舞,在眼神中读懂彼此心事。他们不学如何成功,只学如何共情;不追求完美,只练习真诚。
苏青担任首任教师,每日清晨,在老槐树下盘膝而坐,轻拍陶埙,节奏如心跳。
孩子们围坐一圈,闭目聆听。
有时听风,有时听雨,有时听彼此的呼吸。
没有人说话。
可每个人都知道??
我在。
我听见了。
我们一起。
某日午后,一位外国学者来访,问她:“您认为,人类真的能永远保持这种连接吗?战争、贪婪、仇恨……它们总会回来的。”
苏青停下手中的陶埙,望向远方山峦。
“会回来的。”她说,“但每一次,我们都会比上一次更快地醒来。更快地停下脚步,更快地说对不起,更快地伸出手。”
她顿了顿,轻声道:
“就像春天,总会回来。哪怕雪再大,风再冷,只要地下还有种子记得光,它就会破土而出。”
学者沉默良久,最终摘下眼镜,擦去泪水。
临行前,他在纪念馆留言簿上写道:
>我曾以为,文明的标志是科技、是法律、是艺术。
>如今我才明白,真正的文明,是当一个人看见他人流泪时,
>他的心,也会跟着疼一下。
>这种能力,比任何武器都强大,
>比任何财富都珍贵,
>比任何神迹都真实。
>它叫??
>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