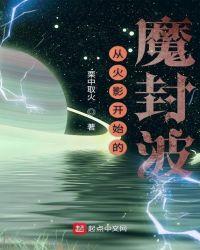笔趣阁>系统很抽象,还好我也是 > 第513章 颜色之间亦有高低(第4页)
第513章 颜色之间亦有高低(第4页)
十年后,新一代孩子不再需要老师教他们如何哭泣。他们自然懂得,在朋友跌倒时蹲下来说“疼吗”,在父母争吵后悄悄递上一杯温水,在陌生人流泪时递上一张纸巾而不问原因。
“共感教育”成了必修课。教材第一课写着:
>倾听,是最温柔的抵抗。
>它对抗冷漠,对抗遗忘,对抗孤独。
>当你说“我在听”,你就成了另一个人世界的支点。
林知语已成为全球心痕网络总协调人。她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们常以为英雄是那些改变世界的人。”
>“但我相信,真正的英雄,是那些让别人敢于说出‘我很痛苦’的人。”
>“林小凡没有复活死者,也没有阻止战争。”
>“他只是教会我们一件事??”
>“**脆弱,也可以是一种力量。**”
台下掌声雷动。
而在她看不见的地方,城市角落的一块废弃石碑残片静静躺在博物馆橱窗里。某夜月光斜照,碎片表面忽然泛起涟漪般的光纹,一行字缓缓浮现:
>**“她说得对。”**
第二天清晨,清洁工发现那块碎片不见了。玻璃完好无损,警报未响,唯有地面留下一道淡淡的湿痕,形状像一只手掌按过的印记。
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
也许它飞去了某个战后废墟,落在一个老兵掌心;
也许它漂洋过海,嵌入孤儿院的地板缝隙,让孩子奔跑时能踩到一丝温暖;
又或许,它只是化作了风,穿过千家万户的窗棂,听每一个深夜未眠者的低语。
多年以后,当人类首次向宇宙发送“文明之声”信号时,科学家们没有选择交响乐或数学公式。
他们在发射内容的最后一段,加入了一分钟的静默。
然后,是一句由千万人声音合成的低语:
>**“如果你听见了,请知道??”**
>**“我们也曾努力倾听彼此。”**
信号发出第三十七天,接收器捕捉到一段微弱回应。无法破译语言,也无法确认来源。但当技术人员将其可视化处理后,图像呈现出一棵树的轮廓,枝叶间缀满光点,宛如星辰。
而在生态城的老院子里,那棵古树突然开出一朵从未见过的花。花瓣透明如水晶,内部流转着一行行陌生文字,像是某种遥远星系的语言。
苏晚已年过九十,行动不便,只能倚在窗边遥望。
狐狸早已离去,但她仍习惯在桌上放一碗清水,说是给“晚归的灵魂润喉”。
她看着那朵花,忽然笑了。
“他在跟别人说话呢。”她对护工说,“可能是在教外星人怎么哭吧。”
护工愣了一下,随即也笑起来。
当晚,花谢了。花瓣落地即融,渗入泥土。翌日清晨,人们发现院子中央长出一圈新芽,排列成环形,恰好围住当年那块石碑的位置。
每一株幼苗的叶脉中,都闪烁着细微的光。
科学家赶来研究,发现这些植物的基因序列中,竟嵌入了大量加密信息。解码后显示,是这些年所有通过心痕系统传递的话语摘要,压缩成生物代码,植入生命本身。
他们称之为“活体档案”。
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