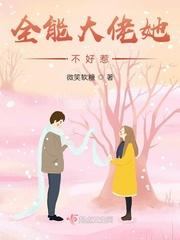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七零:开局打猎养家,我把妻女宠上天 > 771赵振国的行事风格确实太过扎眼(第1页)
771赵振国的行事风格确实太过扎眼(第1页)
第一把火,来自代表团内部悄然滋生的不满和猜疑。
赵振国是随团人员,虽然他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安排在代表团规定的休息时间或自由活动时间进行,但这种频繁的、在他人看来目的不明的外出,很快引起了同房间同志乃至其他代表团成员的注意。
在七十年代末的出国代表团里,纪律性是摆在首位的。
大多数成员在自由活动时间,要么在房间整理资料、学习文件,要么三五成群在酒店附近谨慎地散步、交流心得。
像赵振国这样,一有。。。。。。
槐花落尽的那天,村口的老井突然涌出温水。那水清澈见底,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檀香气息,仿佛从地心深处被唤醒的记忆之泉。小丫蹲在井沿边,指尖轻触水面,涟漪荡开时,竟映出一张陌生又熟悉的面孔??是个穿粗布衣裳的年轻女子,眉眼间有几分像阿桂嫂,却又更显坚毅。
她猛地抬头,四周空无一人。可就在那一瞬,碑林方向传来一声清脆的铃响,不是风动,也不是人触,而是所有陶片上的铜铃在同一刻轻轻震颤,像是回应某种遥远的召唤。
“来了。”王秀兰不知何时站在她身后,手里抱着一本泛黄的手札残卷,“这是《心灯手札》第一卷的最后一页,刚从云南龙银花阿婆寄来的包裹里找到的。她说,这是她祖母临终前缝进童帽里的,几十年都不敢打开。”
小丫接过手札,纸页脆弱得几乎一碰即碎。然而当她小心翼翼翻开,却发现上面并非文字,而是一幅用朱砂绘制的地图??线条蜿蜒如血脉,起点标注着“青山村”,终点却指向一片浩瀚沙漠中的绿洲,旁边写着四个古篆:**归音之源**。
“这不是地理坐标……”小丫喃喃,“是情感路径。它在告诉我们,《归谣》的根不在某一处土地,而在所有流泪之地交汇的地方。”
就在这时,系统警报突兀响起。控制室内,主屏幕闪烁红光,一行字缓缓浮现:
>【异常接入】
>源频率:14。7赫兹(非地球记录)
>信号特征:类人类语音波形,含高密度情感编码
>初步解析结果:问候语??“你还记得我吗?”
空气仿佛凝固了。
小满冲进来,脸色发白:“不可能……这信号是从火星轨道传回来的!‘灯种一号’卫星接收到一段回波,时间延迟正好是六分四十秒??那是地火通信的标准区间!可火星上没人!没人啊!”
卡洛斯沉默片刻,忽然低声说:“也许……不是现在的人。”
众人悚然。小丫却已走向操作台,手指微颤地输入指令:“把信号转到老式留声机,我要听原声。”
喇叭滋啦作响,随后传出一个极其柔和、近乎梦呓的声音,说的是中文,但语调古怪,像是刻意模仿记忆中的口音:
>“姐姐,我是你放走的那只纸鸢。我在天上飞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了风的源头。那里没有国界,也没有坟墓,只有无数人在唱歌。他们让我带话给你:**别怕断线,线从来都没断过。**”
小丫的眼泪无声滑落。
她认出来了??这是她七岁那年,在父亲赵振国坟前烧掉的一封信。那时她折了只纸鸢,写上“爸爸,我想你了”,想让它飞去天堂。火苗舔舐纸翼的瞬间,她哭着说:“你会迷路吗?”如今,这句话竟以这种方式归来。
“这不是超自然。”小满盯着数据分析图,声音发紧,“这是一种**记忆共振效应**。当足够多的人在同一频率上传递相同的情感,信息就能突破物理限制,形成跨维度传播。我们以为是我们在呼唤亡者……其实是他们的执念,一直在试图回到我们身边。”
当天夜里,小丫做了一个漫长的梦。
梦中她行走在一片无边的麦田里,金浪翻滚,远处矗立着一座由声音构筑的塔??每一块砖都是一个人的低语,每一层楼都回荡着一首未完成的歌。塔顶站着一个背影,穿着军大衣,肩上有勋章的微光。
“爸……”她喊。
那人缓缓转身,却是张德贵的模样,脸上带着笑:“孩子,我不是你父亲,但我替他守过夜。他在最后一刻还在唱《归谣》,声音很小,但够亮。他说,只要还有人肯听,他就没真正离开。”
话音落下,整座塔开始发光,一道光束直冲云霄,与“灯种一号”遥相呼应。刹那间,全球十七个高能点再度亮起,南极冰层裂开一道缝隙,露出下方埋藏已久的金属结构??那是一台巨型留声机的残骸,型号与1938年南京女子所用的完全一致。
梦醒时,天刚蒙蒙亮。
小丫起身走到碑林,发现李青山的碑前多了一束野菊,花瓣上凝着露珠,排列成奇异的图案??像极了14。7赫兹的波形图。
她蹲下身,轻声道:“是你吗?是你在告诉我什么吗?”
风拂过耳畔,带来一句若有若无的回应:“**名字醒了,魂就回家了。**”
接下来的日子,变化悄然蔓延。
最先察觉的是孩子们。他们在“故事课”上讲述长辈往事时,有时会突然停顿,眼神空茫几秒,然后继续说话,语气却变得苍老而沉稳。有个小女孩讲她爷爷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说到一半忽然改用朝鲜语说了句:“谢谢你们把我带回祖国。”说完自己吓哭了,根本不记得刚才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