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重生七零:开局打猎养家,我把妻女宠上天 > 772我想要个人(第2页)
772我想要个人(第2页)
小丫的手指抚过父亲的名字,眼泪无声滑落。
图纸详细记载了当年父亲如何带领科研小组秘密研发“情感共振装置”,试图通过特定频率的声音波传递思念与信念,以对抗极端环境下的精神崩溃。但由于技术不成熟,加上政治压力,项目被迫中止,所有资料销毁,参与者遣散。
“可他没放弃。”小满翻到背面,发现一行极小的批注:
>“若此技终有一日重现人间,请交予吾女小丫。她听得见风里的哭声。”
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为什么偏偏是她能唤醒系统,为什么《归谣》会以她的童年记忆为蓝本重构,为什么每一次关键突破都发生在她触碰陶片的瞬间。
她是被选中的,也是被等待的。
当晚,小丫独自来到父亲的新碑前??那是一块由全村人合力打磨的青石,上面没有多余装饰,只有一行朴素的字:
>**赵振国,青山村之子,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归谣守灯人第一代**
她点燃一盏油灯,轻声说:“爸,我来了。”
风忽然停了。
然后,地面传来轻微震动。一道隐藏机关缓缓开启,从碑座下方升起一个密封铁盒。盒内是一盘尚未使用的磁带,标签上写着三个字:
>**《家书》**
小丫颤抖着将它接入便携设备。按下播放键的刹那,整个碑林陷入寂静。
磁带里传来的是多个声音的拼接,像是剪辑而成的语音日记:
>“老赵啊,你说这玩意儿真能传到未来吗?”(男声,陌生)
>“不一定传得到人耳里,但一定能传到心里。”(父亲的声音,坚定)
>“那要是没人听呢?”(女声,年轻,像阿桂嫂)
>“那就等,等到有人愿意开口为止。”
接着,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父亲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只剩他一人:
>“小丫,如果你听到这些,说明你已经长大了。爸爸对不起你,没能陪你长大。但我相信你会比我勇敢,比我善良。你要记住,世界上最厉害的力量,从来不是枪炮,也不是权力,是**记得**。
>记得一个人的笑容,记得一句道歉,记得一场雪落在肩上的感觉。
>只要还有人记得,那个人就没有真正死去。”
磁带戛然而止。
小丫跪坐在地上,抱着录音机久久不动。夜风吹起她的发丝,拂过眼角未干的泪痕。
三天后,联合国派出特别观察团抵达青山村。随行的除了外交官,还有十位世界级语言学家、三位神经科学家和一名盲人音乐家。他们要在七十二小时内评估《归谣》系统的普适性与可持续性,决定是否将其列为“人类非物质文明遗产”。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争论仍无结果。有人认为这是伪科学,有人担心精神操控风险,更有人质疑其背后是否存在军事用途。
直到那位盲人音乐家站起身,摘下墨镜,平静地说:“我不需要看数据。我只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在深夜独自听过《归谣》?不是用耳朵,是用心。”
全场安静。
“我失明三十年了。”他说,“但我第一次听到这段旋律时,看见了颜色。紫色的雾,金色的路,还有一扇木门,门缝透出暖光。我知道那是我家的老屋。我妈去世快三十年了,可我清清楚楚闻到了她煮姜汤的味道。”
他顿了顿,声音微颤:“这不是技术,是回家的路。”
会议室陷入长久沉默。
最终,《青山宪章》获得全票通过,并新增一条补充条款:
>**《归谣》系统及其衍生文化实践,属于全人类共同精神财产,任何国家不得垄断、限制或武器化使用。其核心使命为促进跨时空情感连接、推动历史和解与集体疗愈。**
签字仪式结束后,小丫收到了一条来自南极科考站的紧急通讯。
>“我们在冰层下发现了更多金属残骸,初步判断为一组分布式声波发射阵列,年代测定约为1942年前后。最惊人的是,其中一台设备仍在运行,循环播放一段音频??经比对,正是1938年南京女子所用留声机的孪生机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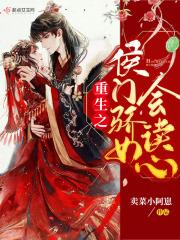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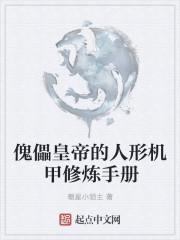
![我拆了顶流夫妇的CP[娱乐圈]](/img/3194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