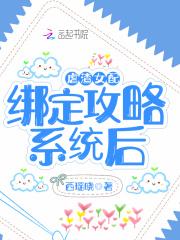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七零:开局打猎养家,我把妻女宠上天 > 779文化认同(第1页)
779文化认同(第1页)
周振邦觉得赵振国就是瞎折腾,这能打动陈家人?开什么玩笑呢?
就靠那封啥“邮票”的诗还有水墨画么?
可让他瞠目结舌的是,两天后,一份精美的请柬送至赵振国手中,邀请他参加一场私人的“茶叙”。
茶叙的地方是一座融合了南洋风情与闽南建筑特色的大宅,古色古香,静谧中透着底蕴。
茶室内,紫砂壶中茶香氤氲。
主人陈延年虽年过花甲,但目光如炬,气度沉稳。
陪同在侧的,还有他的长子陈文翰,约莫三十五六岁,西装革履,毕业。。。。。。
风起于戈壁深处,卷着黄沙掠过干裂的河床。念归坐在一块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石头上,膝头盖着一条褪色的蓝布毯。她望着远处牧童们赶羊的身影,像一幅缓缓移动的剪影,嵌在夕阳熔金般的天幕里。那孩子昨日说的话还在她心里回荡??“阿爸,我今天多分了弟弟一口馍,你放心。”多朴素的一句话,却重得能压弯时光的脊梁。
她轻轻摩挲着手中的陶片录音机,外壳早已斑驳,边角甚至有些碎裂,可它仍稳稳运转,如同她这一生未曾停歇的脚步。她知道,这台机器快要走到尽头了。就像人一样,再坚韧的灵魂也会疲惫,再不灭的记忆也需要安歇。
但她不怕。
因为她已不再依赖它来倾听。
自从晶体融入血脉,她的耳朵便成了通往万千亡魂的门扉。夜里闭眼,她能听见百年前战壕中士兵哼着不成调的小曲;清晨醒来,她会发现枕边湿了一片,原来是昨夜无意识间听到了某个母亲临终前对幼子说“别哭,妈妈去摘星星了”。这些声音不再遥远,它们如呼吸般自然地流淌进她的生命,成为血肉的一部分。
她缓缓起身,将毯子叠好放进背篓,又取出一盏新做的油灯。这是用废弃罐头盒和棉线自制的,简陋却结实。她点燃灯芯,火光跳跃着映在她苍老却清明的眼中。
“走吧。”她对自己说。
这条路她走了几十年。从东北雪原到西南雨林,从东海渔村到西北荒漠,每一寸土地都听过她的脚步声,每一片风都记得她的低语。如今她的腿脚不如从前利索,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可她依旧坚持步行。她不愿坐车,不愿飞,她要一步一步丈量这片她深爱的土地,把光送到那些从未见过灯火的地方。
前方是一座废弃的矿井,铁轨锈蚀,绞车倾倒,入口处塌陷了一半。这里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国营煤矿,三千多名工人在此劳作,其中两百余人长眠地下。事故之后,政府迁走了家属,封死了矿道,连墓碑都没立一座。时间久了,连当地人也只当这里是“不吉利的地界”。
念归却记得他们的名字。
她在小满提供的“心土档案”中读到过那段历史:1958年冬夜,瓦斯爆炸,救援队三天后才打通通道。活着的人蜷缩在角落,怀里还抱着死去工友的遗书。而更多的人,至死都握着镐头,脸朝煤层,仿佛仍在工作。
她提灯走入矿口,脚步轻缓。黑暗如墨汁般涌来,可她并不惧怕。火焰在她手中稳定燃烧,照亮岩壁上模糊的刻痕??那是幸存者用指甲留下的字:“我们在这儿。”
越往里走,空气越冷,湿度越高,水珠从顶棚滴落,敲打在岩石上,发出空灵的回响。忽然,她听见一声极轻的咳嗽。
不是幻觉。
是真实的、带着痰音的咳嗽声,来自前方十步远的一处支巷。
她停下,屏息凝神。
“老李……烟掐了吧,领导来了。”另一个声音响起,年轻些,带着笑意。
接着是一阵??,像是棉袄摩擦的声音,还有火柴划过的细微噼啪。
“操,这破火柴潮了!”第一个声音抱怨,“老子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抽这玩意儿,费钱不说,还呛人……要是能重来一次,我就娶桂花,带她回老家种地去。”
“那你咋不现在就跑?”
“跑了?谁来供我娘吃药?谁给我妹攒嫁妆?咱这命,生下来就绑在煤上了。”
对话戛然而止,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切断。
念归站在原地,泪水无声滑落。
她知道,这不是鬼魂显形,也不是时空错乱。这是“记忆残留”??当强烈的情感与特定空间高度绑定时,会在环境中形成类似声波回放的现象。而如今,因“心土祭坛”的共鸣效应,这类残留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频繁。
她慢慢走向那条支巷,在岔口处跪下,将油灯举高。
“叔伯们,”她低声说,用的是当年矿区流行的山东口音,“我是念归,青山村来的。我知道你们没走远,也知道你们舍不得走。可现在不一样了,外面有人记得你们,孩子们上学念课文时,老师讲过‘五八年矿难’;县志馆里,你们的名字刻在英烈墙上;每年清明,都有学生去旧址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