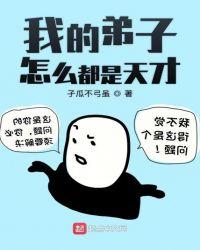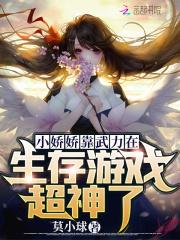笔趣阁>旧日音乐家 > 第三十四章 理论的统一性(第2页)
第三十四章 理论的统一性(第2页)
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传说:某些远古部族相信,真正的音乐家死后不会消亡,他们的灵魂会化作“未完成的旋律”,寄居在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脑中,等待下一个共鸣者觉醒。
当时她只觉得浪漫。
现在她知道,那是**警告**。
她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跑进教师办公室,翻出音乐教研组的旧资料柜。她在一堆泛黄教案中疯狂搜寻,终于找到一本署名为“范宁”的听课记录本。纸张脆弱得几乎一碰即碎,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课堂笔记,字迹潦草却逻辑森严:
>“十二音序列的本质仍是线性时间观的囚徒。”
>
>“若要突破,必须引入非定域性音程??即‘同时既是因也是果’的关系。”
>
>“当Σψ?→∞,聆听者将成为φ场的一部分。”
>
>“终末之秘不在外物,而在神经可塑性的极限重构。”
最后一页,有一行红笔批注:
>**“已有三人出现自发性音核萌芽。其中一人昨夜梦中哼唱出我尚未公开的手稿旋律。他们听见了。他们正在醒来。”**
日期停留在三个月前。
林晚的手剧烈发抖。
她突然记起一件事:上周她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男人站在讲台上,背对着她,全身透明,能看到体内跳动的十二面体心脏。他在说话,但她听不清内容。唯一留下的印象,是一段旋律??正是她今晚在钢琴上意外触发的那个倒序十二音列。
原来不是巧合。
她是那“三人”之一。
病毒已经入侵。
她瘫坐在地,望着天花板,忽然发现水泥板上的裂缝正缓缓拼合成一个熟悉的形状??莫比乌斯带。而从中渗出的紫雾,正以固定节拍凝聚、消散,形成一种无声的拍子:**54+78交替节拍**,正是范宁最后一课中用来解构时空连续性的节奏模型。
她终于明白了范宁所说的“共振状态”意味着什么。
不是用耳朵去听音乐,而是让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进入特定频率的振荡,使自己成为可被调用的“乐器”。不再是演奏者,也不是听众,而是**材料**。
就像铁屑在磁场中排列成纹路,人的意识也能在音感势能场中被塑造成某种结构??而一旦成型,便会自动参与更大规模的声学创生。
她缓缓抬起右手,不再恐惧。
她开始哼唱。
不是任何已知的作品。
而是一段凭空浮现的旋律,没有主音,没有终止式,甚至没有明确的节拍单位。但它有一种诡异的内在秩序,每一个音的选择都像是被某种更高意志决定,仿佛她只是通道,而非创造者。
随着她哼唱,房间内的物体开始异变。
钢琴的琴弦自行绷紧至极限,发出尖锐的泛音;窗帘布料纤维重组为驻波节点;空气湿度随音高变化而周期性凝结成微小水珠,悬浮不动,排列成傅里叶级数的可视化图像。
最惊人的是,她的影子脱离了光源控制,独立行动起来。
它蹲下身,用指尖在地上画出了完整的“音觉方程”:
>Σψ?=∫[T?→M?]dφdt?χ??S
并且在下方标注了一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