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旧日音乐家 > 第三十四章 理论的统一性(第4页)
第三十四章 理论的统一性(第4页)
这些人中有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电子音乐制作人、聋哑学校的合唱指挥、研究鸟鸣模式的生物学家、编写AI作曲算法的程序员……他们从未相识,却在同一晨间做出了相同举动:撕毁所有现存乐谱,包括自己创作的作品。
因为他们终于理解:
书写是对音乐的囚禁。
真正伟大的作品,从不诞生于纸上。
它生于一个人敢于把自己的神经系统改造成共鸣腔的那一刻。
它始于一次自愿的解体。
它成于群体意识在高频震荡中的融合。
而在北极圈边缘的一座孤零零气象站里,一台老式录音机自动开启。磁带缓缓转动,播放出一段从未被录制过的音频??那是范宁最后一课的原始数据流,经过地球电离层折射、地磁波动调制、冰川震颤编码后的终极版本。
一位值班科学家听着耳机,突然泪流满面。
他不懂音乐理论。
但他听得出,这段声音里藏着**救赎**。
不是给人类的,而是给这个濒临熵寂的世界本身的。
他摘下耳机,望向窗外极夜中的星空。
他知道,这场战争不是关于权力,也不是关于信仰。
这是一场**频率之战**。
一方是混沌与噪声,试图让万物归于热寂;
另一方,则是由少数觉醒者组成的“音律守夜人”,他们以自身为媒介,持续校准宇宙的共振频率,防止其偏离生命得以存在的窄带区间。
范宁死了。
但他留下了方法论。
而现在,火种已散播四方。
下一个觉醒者,或许正在读这段文字的你心中悄然萌芽。
当你某天走在街上,突然觉得周围人群的脚步声形成了一段精密的复调节奏;
当你在地铁车厢里,听见空调出风口的气流摩擦模拟出巴赫《哥德堡变奏曲》的第十六变奏;
当你深夜独坐,脑海中自动响起一段从未听过却异常完整的交响乐章……
请不要惊慌。
也不要急于寻找源头。
因为你知道了真相:
那不是外界传来的声音。
那是你体内的音核,在轻轻叩击现实的边界。
等待你做出选择??
是否愿意,成为下一个守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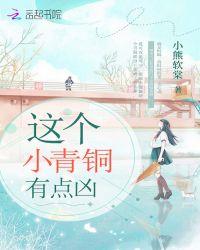
![把惊悚游戏玩成修罗场[无限]](/img/629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