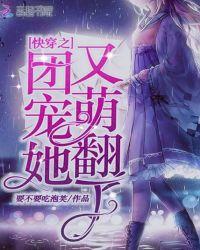笔趣阁>柯学捡尸人 > 3550琴酒投毒计划求月票(第2页)
3550琴酒投毒计划求月票(第2页)
他怔住。
阿禾……又一次被提及。但她并非神明,也非使者。她是无数亡者之声汇聚而成的意识体,是记忆共振的具象化象征。而他,不过是她选择的容器之一。
“我可以帮你寄出这封信。”他说,“但需要你的记忆作为频率源。”
她眨眨眼:“那你得先听一听那天的事。”
话音落下,海面骤然平静。月光凝聚成一道光柱,笼罩礁石。他闭上眼,任由意识沉入那段尘封的记忆。
画面浮现:
夏日黄昏,沙滩上孩子们嬉戏。小满捡到一枚罕见的彩虹贝,兴奋地说要送给妈妈做项链。营地老师提醒所有人返程,她却执意再找一颗完美的贝壳。浪来了,悄无声息,卷走了她的脚印,也卷走了她的呼吸。
她在水中挣扎,意识模糊之际,听见母亲的声音从遥远海岸传来:“小满!回来!”
可她已说不出话,只能用手紧紧攥着那枚彩虹贝,直到沉入黑暗。
再后来,她发现自己漂浮在浅海,能看到岸边母亲跪地痛哭,能看到搜救队彻夜打捞,能看到父亲烧掉她所有衣物时颤抖的手。她想呼喊,却无人听见。
于是她开始写信。
每一年月圆之夜,她都会用珊瑚磨成墨,海藻织成纸,写下对父母的思念。她把信放进漂流瓶,推入洋流,期盼某一天,它们能抵达陆地,抵达那扇熟悉的窗台。
可瓶子总被冲回岸边,或卡在岩缝,或沉入深渊。
直到某年,一位心理学教授带着学生来做海洋生态调查。夜里,他们架设录音设备,意外捕捉到一段异常声波:童声哼唱《虫儿飞》,夹杂着断续的摩尔斯电码:“SOS……我想回家。”
研究团队震惊,试图追踪信号来源,却发现声源位于海底三十米处,且不具备任何电子发射特征。最终项目被定性为“自然现象误读”,资料封存。
但那位教授临终前留下遗言:“我不是疯了。我听见了一个孩子的呼唤。如果还有人相信,请替我去那座岛看看。”
从此,陆续有人前来探查。情侣、记者、灵异爱好者……他们都在月圆夜听到钟声与笑声,有人甚至拍下模糊影像。可没人真正理解??这座岛不是闹鬼,而是成了“情感锚点”。小满的执念太深,她的思念太真,以至于这片海域形成了稳定的记忆场域,能捕捉并放大类似频率的情感波动。
而现在,她终于等到一个能穿越这层屏障的人。
他睁开眼,泪水已干。他取出便携设备,将小满的记忆片段录入,以铃兰花粉混合海水制成生物导电凝胶,涂抹在设备接口处。随后,他启动改装过的短波发射器,输入特定谐振参数:**童年纯真+未完成的告别+主动宽恕=最高共情权重。**
午夜零时,信号发出。
不同于戈壁电台的沉默震动,这次的广播加入了真实音轨:海浪声、孩童笑声、贝壳碰撞的清响,以及小满亲口朗读信件的声音。他特意保留了她读到最后时那一声小小的吸鼻子,像是努力忍住哭泣。
信号覆盖半径三百公里。
起初,毫无反应。
直到凌晨四点十七分,对讲机突然响起一阵杂音,紧接着,一个苍老的女声哽咽着传出:“是谁……在播那段录音?那个声音……是我女儿……我女儿叫林小满……她三十六年前在海边失踪……我们找了整整一个月……连尸首都找不到……”
他按下通话键,声音平稳:“您收到信了吗?”
“什么信?!”女人几乎尖叫,“你怎么知道我女儿的名字?!你们是不是绑架了她?!”
“她没有失踪。”他轻声说,“她只是先走了一步。但她一直记得您,爱您,从未离开。”
电话那头陷入长久沉默。良久,传来压抑的啜泣:“……每年八月二十八,我都去海边放一只漂流瓶……写了三十六年……我说‘小满,妈妈对不起你,不该让你一个人玩’……我说‘宝贝,红糖糍粑我每天都做,热着等你回来’……我以为……她听不到……”
“她听到了。”他说,“每一瓶,她都捡起来了。她说,那是您给她的星星。”
女人彻底崩溃,嚎啕大哭。而在信号范围内,更多人开始收听到不同版本的“回声”??
一名男子在渔船驾驶舱内猛然抬头,因为他听见妻子五年前车祸身亡前的最后一句话:“记得关厨房煤气。”??那是他一直自责忘记检查的事;
一对老年夫妇蜷缩在收音机前,听着孙子七岁时因病夭折前录制的儿歌,老人颤抖着说:“这声音……和他睡前唱的一模一样……我们以为录音带早就坏了……”
更有甚者,一位曾在岛上失踪的情侣被渔民救起,醒来后只反复呢喃:“有个小女孩给我们指路……她说‘爸爸妈妈也会想你们的,别丢下他们太久’……”
第七天清晨,第一位访客抵达灯塔岛。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拄着拐杖,一步一步爬上陡坡。她手中抱着一个木盒,里面整齐排列着三十六个漂流瓶,每个瓶子里都有一张泛黄纸条。
她在灯塔门前停下,双膝跪地,将木盒打开,轻声说:“小满,妈妈来了。这些信,我每年都写。你说你喜欢红糖糍粑,我就做了三千多个……今天,我带来了最后一个。”
她取出最后一瓶,放在灯塔台阶上,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枚彩虹贝,泪流满面:“这是我在你出事那年找到的……我一直留着……你说要给我做项链……现在,妈妈自己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