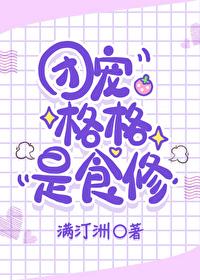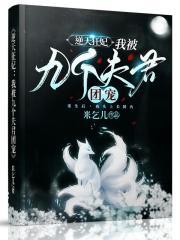笔趣阁>我真没想下围棋啊! > 第四百九十九章 他在支撑着我(第2页)
第四百九十九章 他在支撑着我(第2页)
一曲终了,满室寂静。我听见自己颤抖的声音:“我能……录下来吗?”
伊布拉点点头:“可以。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告诉外面的人,我们不是可怜。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
我重重点头,按下录音笔。
当晚,我们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夜里风更大了,吹得窗户咯吱作响。沈砚之坐在床沿,默默摆开围棋盘,一颗黑子落在天元,又一颗白子回应于小目。他在复盘普路那局棋,动作极慢,像是在咀嚼每一个手势背后的重量。
“你觉得他们能听懂吗?”我问他,“这些孩子,从来没有见过棋盘的样子。”
他抬头看我,眼神平静:“可他们听得见落子的声音。你知道‘声纳’吗?蝙蝠用声音描绘世界。也许,我们可以教他们用棋子的位置发声??比如,高位置代表高音,低位置代表低音;黑子是鼓点,白子是旋律。让围棋变成一种可触摸的乐谱。”
我怔住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向马阿娘提出了这个想法。她听完,久久未语,最后只说了一句:“伊布拉小时候最爱摸地图。他说,手指走过的地方,就是他去过的地方。”
于是,我们开始尝试。
我们将棋盘平铺在桌上,用不同质地的棋子代替传统黑白??黑子是光滑的玛瑙,白子是粗糙的磨砂陶瓷。每颗棋子底部都贴有微型凸点标识位置坐标。孩子们围坐一圈,由沈砚之引导,用手感知棋盘格局。
“现在,我要放一颗黑子,在右上角。”他轻声说,将棋子轻轻放下,“它的声音,应该是低沉的鼓。”
伊布拉伸出手,触碰到那颗棋子,随即点头:“像父亲赶牛进圈时的脚步。”
“再来一颗白子,在左下。”我接道,“清脆一点,像雨滴。”
一个小女孩摸到后,笑了:“是奶奶摇铃叫我吃饭!”
我们继续推进。当形成一条斜线时,孩子们自发哼起了旋律;当围成一块实地,他们用拍手打出节奏。渐渐地,一场“棋乐合奏”诞生了??棋局不再是胜负之争,而是一场集体创作的声音诗篇。
中午时分,伊布拉突然提出:“我想下一盘‘独白’。”
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一个人执双色,表达内心最深处的情绪。
他坐下,深吸一口气,开始落子。
第一手,黑子天元??**“我是存在的。”**
第二手,白子三三??**“可我不知道我在哪。”**
第三手,黑子跳至边路??**“我想走出去。”**
第四手,白子镇头压制??**“世界说我不能。”**
棋局越走越激烈。他的手指在棋盘上游走,速度快得惊人,仿佛压抑多年的话语终于找到了出口。他用“断”表示挣扎,用“靠压”诉说压迫,用“大飞”象征逃离的渴望。而每当陷入困境,他总会停顿片刻,指尖轻轻抚过那道烫伤疤痕,然后再落下一子??**“我还活着。”**
最后一手,他将一颗白子轻轻放在中腹,与黑棋大龙紧紧相贴。
全场静默。
我低声翻译:“这手……是在拥抱自己。”
伊布拉摘下耳机(那是他用来记录声音的习惯),缓缓打出一段手语??这是他从普路视频中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