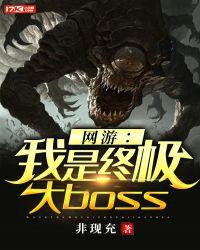笔趣阁>春色满棠 > 第470章 心疼心疼你男人(第3页)
第470章 心疼心疼你男人(第3页)
>审讯员:“你们传播反动诗歌,煽动青年思想混乱,可知罪?”
>林知微:“我们只是写了真话。”
>白露:“如果真话是反动,那这个国家就没有正义。”
>(打斗声)
>林知微(临被拖走前,高声):“记住!总有一天,会有人替我们把课上完!”
这段录音通过忆纸网络公之于众后,全国十三所高校自发组织“补课行动”,在同一时间复刻当年被中断的课程。北京一所中学甚至还原了苏晓父亲的最后一堂课,邀请其女儿站上讲台,完成那句未说完的结语:
“教育的目的,不是制造顺民,而是唤醒灵魂。”
话音落,全校师生齐声回应:“我们听见了。”
这一刻,忆归桥再次发光,亮度前所未有。桥面浮现出十三道人影,正是当年守护静语窟的教师群体投影。他们并肩而立,向世人深深鞠躬。
陈砚站在桥头,望着这一切,忽然感到胸口一阵温热。他伸手探入衣袋,发现那朵干花竟已复活,花瓣舒展,散发淡淡清香。更令人震惊的是,花心处浮现出一行微型文字,以古篆书写:
>春色满棠,不在枝头,而在人心。
>凡有所忆,皆可归来。
>??守门人留
他抬起头,望向天空。云层裂开,月光倾泻,照在每一寸曾被遗忘的土地上。
他知道,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仍有城市拒绝接入忆纸网络,仍有家庭藏匿着不愿面对的过去,仍有孩子在学校里被教导“有些事不要问”。
但他也明白,火种已燃,桥已建成,门已开启。
只要还有人愿意讲述,就永远有人能够回来。
夜深时,他回到书院,坐在棠树下,打开笔记本,写下新的计划:
>启动“春录计划”:
>将《春录》全文公开出版;
>在全国设立一百零八所“真话学堂”;
>每年春分,举办“补课日”,由幸存者后代接力完成中断的课程;
>建立“守门人档案馆”,收录所有通过忆纸网络回归的声音。
写完,他合上电脑,轻声说:“我说了。”
风穿过树叶,带回一声温柔的回答:
“我们都在听。”
远处,一个小女孩牵着母亲的手走过桥面,忽然停下,指着棠树说:“妈妈,那个穿红裙的姐姐,对我笑了。”
母亲怔住,随即蹲下身,紧紧抱住孩子。
而在无人看见的角落,一片金叶悄然飘落,化作一枚书签,静静躺在《承音册》翻开的一页上。那页写着:
>“记忆不死,唯惧无人呼唤其名。
>故我立誓:
>以身为灯,以言为火,
>照彼幽暗,迎其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