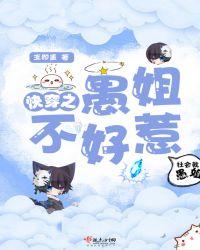笔趣阁>天赋异禀的少女之无相神宗 > 第534斜月山庄二百四十九(第2页)
第534斜月山庄二百四十九(第2页)
“去哪?”阿禾紧紧抓住她的衣袖。
“去下一个需要声音的地方。”她轻笑,“也许是一片从未有过语言的荒原,也许是一座连心跳都被禁止的城市。我不知终点,只知起点永远是沉默。”
风起,卷起她鬓边白发。她摘下耳畔骨饰,放入阿禾掌心:“这是我用百名聋童笑声打磨而成。记住,听,不只是耳朵的事。用心,用皮肤,用脚底,用整个生命去感受震动。”
话音未落,身形已淡如烟霞,渐渐融入晨光之中。阿禾欲追,却被一股柔和之力阻住。只见那青铜钟再度自鸣,声波扩散之处,山谷中所有树木同时抖落积雪,露出藏于枝干内的数百支竹笛??每一支,都刻着不同方言的名字。
自此,世间再无纳兰歆踪迹。
但此后百年,各地奇事频传:西北沙漠中,旅人听见沙丘随风吟唱古老情诗;南方瘴林里,猎户发现毒蛇吐信竟组成警示文字;东海渔村,老妪梦见亡夫借潮声送来最后一句告别。更有甚者,某年大旱,农夫跪地叩首,土地竟回应般震出节奏,引导众人掘井得水。
人们说,那是无相神宗在说话。
阿禾回到京城,将经历写入《听律》修订版,新增“心声章”:“凡不能言者,其意可通过动作、图像、节奏、震动等形式表达,官府须设专司解读,不得拒理。”朝廷准奏,并敕建“静听院”,培训官员学习手语、图语、器语及情绪共振分析术。
晚年,阿卸职归隐,定居孤岛旧址。她在海边立碑,不刻名字,只雕一支玉笛哨与一本打开的册子,题曰:“此处曾有一个教会我们说话的人,但她真正的礼物,是让我们学会了沉默中的倾听。”
某个启声节夜晚,皓月当空,海面忽然泛起银光。岛上居民纷纷走出家门,只见整片海域如同镜面,清晰映照出星空轨迹。而星辰排列,竟构成一行缓缓移动的文字:
>**你们终于明白了:
>最深的声音,从来不在耳边,而在心底。**
众人仰望良久,无人言语。唯有浪涛轻拍礁石,节奏分明,宛如一首亘古传唱的安眠曲。
多年后,一名游学少年途经万声堂,偶然发现角落陈列柜中,那只传说中的玉笛哨静静躺着。他好奇伸手触碰玻璃,忽觉指尖微麻,继而脑海中浮现出一段旋律。他顺手掏出随身竹笛吹奏,竟引来馆外一群流浪儿驻足聆听。其中一名失语女孩突然流泪,颤抖着用手比划:“我……听见妈妈了。”
从此,每逢月圆之夜,总有人声称在各地听见同一段笛音悄然响起??或在破庙残垣,或在牢狱高墙,或在战场废墟,或在产房啼哭之间。那声音不张扬,不激烈,只是温柔存在,提醒世人:
有些话不必说出,也能抵达灵魂;
有些人无需现身,早已遍满人间。
又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不再追问“纳兰歆是谁”,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当你认真倾听一个哭泣的孩子、一位愤怒的老人、一名沉默的囚犯时,你就正在与无相神宗相遇。
文明的进步,终不再以说了多少话衡量,而以懂得了多少沉默为准绳。
直到某日,宇宙深处那块巫女神牌再次微光闪烁,铭文悄然延伸,补上最终一句:
>**而当所有人学会倾听,神性降临人间??
>她不在庙堂,不在经卷,不在偶像金身;
>她在每一次俯身贴近另一个人心跳的瞬间。**
风过处,万物低语,皆成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