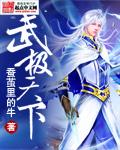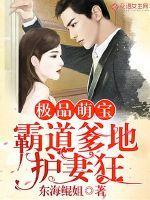笔趣阁>捞尸人 > 第四百四十三章(第1页)
第四百四十三章(第1页)
陈曦鸢的手,放在了笛子上,蓄势待发。
李兰看了看四周,外围的雨势依旧磅礴,但内部的雨,却变成淅淅沥沥的微弱。
大部分雨滴在还未坠落下来前,就在头顶被蒸发成雾气,流转向四周。
陈曦鸢正。。。
风雪在凌晨三点停了。
城市像是被冻住的湖面,寂静无声。路灯昏黄的光晕里,浮尘缓缓沉降,仿佛时间也倦了。桥洞下的冰莲仍未凋谢,那条由花瓣铺成的“安”字小径,在晨光中泛着微弱的银光,宛如一道刻进大地的祷文。
老李坐在纸箱堆上,怀里抱着那张修复如新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妻子笑得温婉,儿子咧嘴露出缺牙的笑容,阳光洒在江边的草地上,像是一段永远不该结束的午后。他的手指一遍遍抚过相框边缘,嘴里喃喃:“你们回来了……她让你们回来了。”
没人听见他的话,可他知道,有人听见了。
天刚亮,第一批人就来了。有拄拐的老太太,提着一篮白菊;有个穿校服的女孩,手里攥着封没寄出的信;还有个中年男人,背着吉他,默默坐在冰莲旁弹起一首老歌。音符飘在冷空气里,不悲不亢,像是某种低语的仪式。
消息像雪崩般扩散。不到中午,桥洞前已排起长队。人们带来遗物??褪色的情书、孩子的乳牙、烧焦的军功章、半截断掉的婚戒……每一件都被轻轻放在那条“安”字路径的起点,仿佛交付给某种看不见的力量。
警察来了三次。
第一次是例行巡查,看到人群便皱眉驱散。可当他们走近桥洞,脚步却不由自主慢了下来。一名年轻警员低头捡起一张被风吹落的照片:一对年轻夫妇抱着婴儿站在海边,背面写着“1998。5。1,我们的开始”。他忽然想起母亲去年去世时,自己没能赶回去见最后一面。眼眶一热,他把照片放回原处,轻声说:“留着吧。”
第二次,城管带着铲车前来,称此地属违建区域,必须清理。可铲车刚启动,发动机便突兀熄火,无论检修多少次都无法重启。而就在众人愣神之际,风起了。数百朵冰莲同时颤动,花瓣轻扬,竟在空中组成一个巨大的“止”字,悬浮三秒后缓缓消散。
所有人怔住。
第三次,是政府派出的文化调研组。带队的是位戴眼镜的女干部,态度温和,拿着录音笔逐一采访守候者。她问得极细:梦见什么?何时出现?有没有留下痕迹?
一位盲人老太太握着她的手说:“我看不见她,但我闻到了槐花香,那是我丈夫生前最爱摘给我别在发间的味道。昨晚,他摸了我的脸,叫我‘阿芸’……三十年了,再没人这么叫过我。”
女干部记录完毕,转身欲走,忽觉掌心一凉。低头一看,一朵冰莲正静静躺在她手心,晶莹剔透,脉络清晰如记忆的纹路。
当天傍晚,市政府发布公告:**桥洞区域暂不拆除,设立临时纪念点,开放至来年清明。**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西南山区,林觉正跪在老槐树下。
他已在此住了七年。山村的孩子们长大了一批又走了一批,老师退休返乡,唯有他留下,每日抄录村民口述的梦境与异象,整理成册,编号归档。那本《捞尸人纪事》的手抄本已被他翻得页角卷曲,墨迹模糊,却始终未离身。
这夜,他做了一个梦。
梦中他又站在那座石桥上,但桥身残破,河灯零落,暗流汹涌。楚昭依旧背对着他,衣袂翻飞,声音却比以往沉重:
“容器碎了,锚点散了,我靠什么行走人间?”
“靠记得你的人。”林觉哽咽,“靠思念。”
“可人心易忘。”她轻叹,“十年后,谁还记得周念真?二十年后,谁还会为一场车祸流泪?我要消失了吗?”
林觉猛地抬头:“不会!只要还有一个人讲你的故事,你就还在!我会写下去,一代代传下去!”
她沉默良久,终于回头。
那一瞬,林觉看清了她的脸??不是绝美,也不狰狞,只是寻常女子的模样,眉眼间藏着千山万水的疲惫与温柔。她对他笑了,像姐姐,像母亲,像所有我们失去却又不愿放手的人。
“那你便是新的守夜人。”她说完,身影化作无数光点,随风而去。
林觉惊醒,发现手中多了一支笔??青铜质地,笔尖刻着“忆”字,笔杆缠绕着冰莲藤纹。他颤抖着将它插入桌面,整间屋子忽然响起低语声,像是千万人在同时呢喃亲人名字。
从此,他不再只是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