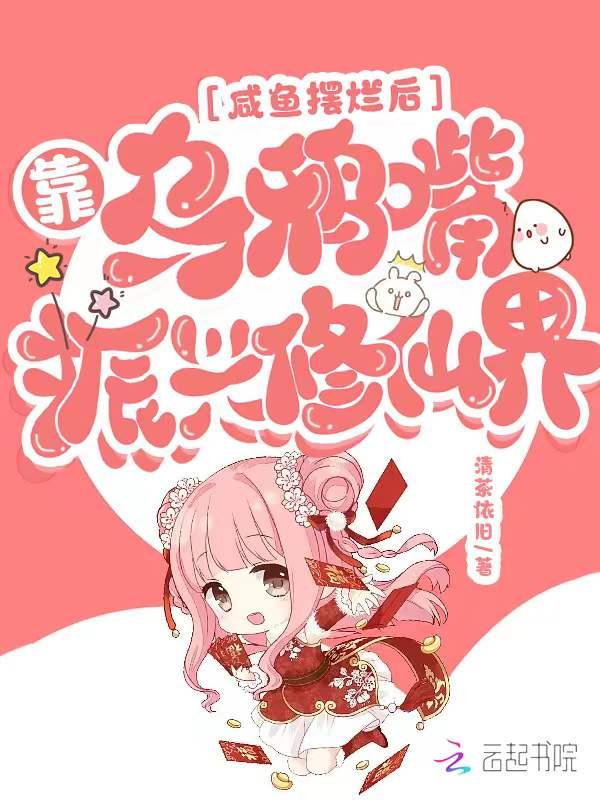笔趣阁>捞尸人 > 第四百五十二章(第1页)
第四百五十二章(第1页)
翟老的电话很简短,只是告知了李追远他到玉溪的具体时间。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日程对接,但电话来的时机却真的很巧妙。
李追远挂断电话,润生正在收拾供桌,清理火盆里的纸灰时,可以发现先前少年丢进去。。。
夜风拂过河面,第九盏灯的暖白光芒在水波中轻轻摇曳,像一颗跳动的心脏。陈知秋仍坐在石碑旁,掌心炭心微温,仿佛有脉搏与她同步。孩子们早已回家,纸灯的余光却还在河底闪烁,如同沉入梦境的星子,缓缓游向桥的彼端。
她忽然察觉,河水流动的方向变了。
原本自西向东的缓流,此刻竟逆向而行,水面泛起细密涟漪,一圈圈朝光桥中心汇聚。九盏灯同时震颤,焰火拉长成丝线,交织成一张半透明的网,悬于河心上空。网中浮现出模糊影像??一座青铜门,深埋于河床之下,门扉紧闭,两侧刻着古老符文:**“言未尽者,不得归;声未闻者,永徘徊。”**
她心头一紧。
这是《守夜人录》里从未记载的禁地。母亲临终前攥着她手腕时,嘴唇蠕动,似乎想说的,就是这个?
她站起身,赤足踏入水中。这一次,河水不再刺骨,反而如体温般温和,仿佛在迎接她。每走一步,脚底便生出一朵冰莲,承托她的重量,一路延伸至桥心。当她踏上第九盏灯正下方时,整座光桥骤然静止,连风都凝滞了。
青铜门缓缓开启,一道低沉女声从中传出,带着千年沉积的疲惫:
>“你听见我了吗?”
不是问句,而是验证。
陈知秋张口,却发现声音被抽离,只能以心回应:“我听见了。”
门内走出一人。
并非亡魂,也非活人。她穿着民国年间的女学生装,裙角破损,发辫松散,左眼失明,右眼却清澈如泉。她怀里抱着一本烧焦一半的日记本,指尖死死抠住封面,指节发白。
“我是第一代守夜人。”她说,“也是第一个‘听者’。”
陈知秋呼吸一滞。
传说中,楚昭效应始于一场百年不遇的极寒之夜,江河倒流,死者开口。可没人知道,那夜真正点燃第一盏灯的,是一位名叫沈清梧的女子。她在战乱中失去全家,独自守着渡口三年,只为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某夜,她听见河底传来丈夫的声音:“清梧,替我说完那句话。”
她点了灯。
从此,亡者得以诉说,生者得以倾听。但她自己,却被世人视为疯妇,驱逐出境,最终投河自尽。她的名字,被后人从所有记录中抹去,只留下一句残语:“若有人再听见,请替我说完。”
“你说的……是哪句话?”陈知秋轻声问。
沈清梧颤抖着翻开日记,最后一页写着一行血字:
>“对不起,没能活着见到你最后一面。”
“那是我对父亲说的。”她泪流满面,“他死于炮火那天,我在城里教书,没来得及赶回去。等我到家,只剩一具焦黑的尸体。我想告诉他我有多后悔,可他已经听不见了……直到那晚,我在河边听见他的声音,一遍遍重复:‘女儿,你说啊。’”
陈知秋忽然明白了。
所谓“捞尸”,从来不只是打捞溺亡者的躯壳。真正的尸体,是那些卡在生死之间、因一句话未说完而无法安息的灵魂。而守夜人,便是那个愿意弯下腰,拾起这些破碎言语的人。
“你为何现在出现?”她问。
“因为第十盏灯即将觉醒。”沈清梧指向河底深处,“第十河之下,埋着一万具‘未完成’之尸。他们不是死于意外或疾病,而是死于沉默??爱未表达,恨未化解,道歉迟来三十年,告白压在心底一辈子。他们的声音积压成河,终将冲垮现世与彼岸的界限。”
陈知秋望向炭心,它正剧烈震动,映出无数画面:
一位老兵跪在无名墓前,哭喊“战友,我对不起你”;
一对夫妻在车祸前争吵,妻子最后一句是“滚”;
一个少年跳楼前,在手机备忘录写下“其实我只是想抱抱妈妈”。
这些声音从未消失,只是无人听见。
“所以……第十代守夜人,必须能承载所有未说出口的言语?”她喃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