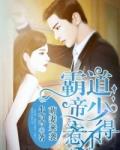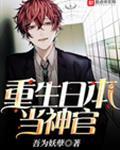笔趣阁>刚想艺考你说我跑了半辈子龙套? > 第491章 电影局的会议(第2页)
第491章 电影局的会议(第2页)
>我是陈屿的女儿。父亲走前一个月,每天都在写东西,说是‘还债’。我不懂艺术,也不懂你们之间的故事,只知道他临终前反复念叨一句话:‘告诉林默,我不是不信他,是我怕自己配不上那份信任。’
>
>他留给你一个U盘,藏在他书房地板下第三块松动的木板里。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上了讲台,就请你打开它。
>
>他说,那不是道歉,是接力。”
林默攥着信纸的手微微发抖。他连夜驱车赶往城郊的老宅??陈屿生前居住的房子已被女儿出租,但他说明来意后,女孩还是带他进了书房。地板撬开,果然有一块暗格,里面静静躺着一个黑色U盘。
回到工作室已是凌晨三点。他插上U盘,屏幕上跳出一个视频文件,标题只有两个字:《补课》。
点击播放,画面出现陈屿坐在老旧教室里的身影。背景是艺考培训班的墙报,日历显示日期是二十年前的冬天。他穿着旧毛衣,神情疲惫却认真。
>“林默,如果你看到这个,说明我已经不在了。也说明……你终于愿意面对曾经被你称为‘失败’的那段时光。
>
>我对不起你。当年你说要改剧本,要用真实的独白代替标准范文,我坚决反对。我说考场不是试验场,评委要看的是规范、是技巧、是可控的情绪输出。我说你太理想主义,会毁了自己。
>
>可我现在明白了,是你对的。
>
>那天你念完那段关于父亲缺席的独白,全场沉默,不是因为你演砸了,是因为所有人都被刺痛了。包括我。我只是不敢承认。
>
>后来你退学,我听说你去片场跑龙套,扛摄像机、搬道具、熬夜剪片子,干遍了最苦的活。我以为你是赌气,现在才知道,你是把自己扔进了生活的底片堆里,一点一点学会怎么拍出真实的眼泪。
>
>所以,请你原谅那个固执的老头。也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当你站在讲台上,不要教学生‘该怎么哭’,而是告诉他们??
>真正的表演,是从不再掩饰脆弱开始的。”
视频结束,黑屏良久。林默坐在黑暗中,手指抚过屏幕边缘,仿佛想触碰那个已逝去的身影。窗外雨又下了起来,敲打着屋檐,像无数细小的脚步声。
第二天清晨,他带着U盘去了教育部影视学院。评审委员会正在召开《非虚构表演》课程实施研讨会,多位专家质疑课程“过于情感化”“缺乏方法论支撑”。争论正激烈时,林默推门而入,将U盘插入投影设备。
“各位,我想放一段二十分钟的视频。”他说,“这不是教学大纲,也不是学术论文。这是一个老师,在生命尽头,给另一个学生的补课。”
会议室安静下来。视频播完,没人说话。良久,一位白发教授摘下眼镜,低声说:“我们错了。真正的教育,不该是用来筛选合格演员的筛子,而应是接住每一个坠落灵魂的网。”
课程方案全票通过。附加决议写道:自本学期起,设立“陈屿纪念奖学金”,资助致力于非虚构影像创作的青年学子。
春末的最后一场雨过后,天空湛蓝如洗。“记忆剧场”正式公演的日子到了。康复中心的小院被布置成露天剧场,三千张门票早在一周前就被领空。观众中有家属、医护、学生,也有专程赶来的媒体记者和影评人。
开场前半小时,林默站在后台,最后一次核对流程。忽然有人拍他肩膀,回头一看,竟是当年艺考评委之一的老李。那人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评分表,声音沙哑:“我查了档案……你那次艺考,我打了最低分。理由是‘表现力不足,缺乏舞台掌控’。”
林默笑了笑:“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