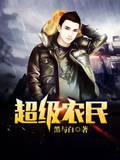笔趣阁>影视编辑器 > 第189章 戚继光(第2页)
第189章 戚继光(第2页)
之私。”
“第二步,曰分化与拉拢。”第二根手指伸出,“官绅一体纳粮’直指士大夫之利,阻力必然最大。然士绅并非铁板一块。可明发上谕,言明新政旨在‘均平赋役,富国强兵,并承诺,凡主动配合清丈、如实纳粮之官绅,其子
弟在科举入仕、考评升迁上,可予以适当优容。同时,对皇亲国戚,功勋贵戚,可由陛下亲自召见,许以其他政治或经济补偿,争取其至少保持中立。此乃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
说到这里,苏宁停顿片刻,语气变得无比凝重: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曰‘立威与固本。”他伸出第三根手指,“待到试点见效,舆论已成,部分势力已被分化,便到了全面推行之时。届时,必然会有效仿徐阶之辈,隐匿田亩、对抗新政。陛下需下定决心,擒贼先
擒王,选择一两个势力庞大,罪行确凿的典型,无论是阁老家乡的豪族,还是某位国公的田庄,都要以雷霆手段,坚决查办,抄没家产以儆效尤!同时,必须确保新军及‘大明超市’物流体系牢牢在手,此乃稳定民心、输送物资、
应对不测之根本。”
最后,苏宁总结道,目光灼灼:“陛下,此三步行之,快则十年,慢则二十载,急不得,也乱不得。需要的是陛下的耐心、定力,以及。。。。。。在关键时刻,敢于亮剑的决心!不知陛下,是否做好了打这场持久战的准备?”
万历听着苏宁抽丝剥茧般的分析,从造势到试点,从分化到立威,每一步都既有远见又有可操作性,但每一步也都充满了风险。
他靠在龙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袍角,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暖阁内,只剩下炭火偶尔爆开的噼啪声。
暖阁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万历尚在消化那三步方略背后的千钧重量,却见苏宁忽然整了整衣袍,以从未有过的郑重姿态,向着御座深深一揖。
“陛下,”苏宁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方才臣所陈三策,看似环环相扣,实则步步惊心。摊丁入亩与官绅一体纳粮,这是要动摇千年来的根基。当那些世家大族发现世代享有的特权即将不保时。。。。。。”
他刻意停顿,让每个字都重重落下:“难保不会有人铤而走险。”
万历闻言眉头紧锁:“苏先生是说。。。。。。”
“臣是说,刀剑或许不敢直指陛下,但臣这个首倡者,必将成为众矢之的。”苏宁的声音冷静得近乎残酷,“下毒、刺杀、制造意外。。。。。。这些手段,史书上记载得还少吗?当年商鞅变法,最后落得什么下场,陛下想必比臣更清
楚。”
他向前一步,目光灼灼:“臣个人生死不足为惧,但若臣在这个时候不明不白地死了,新政必将夭折,朝野再无人敢言改革!届时,陛下的一番宏图大志………………
话未说完,但其中的意味已不言而喻。
万历猛地站起身,在暖阁内急促踱步。
他当然明白苏宁这番话的分量-这绝非危言耸听。
想到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测,年轻的皇帝额角已渗出细汗。
“臣恳请陛下,”苏宁适时开口,“准许臣招募五十人的私人护卫,护卫府邸,保护家小安全。这些护卫需允许佩戴兵刃,在京城内享有有限度的自卫权。”
万历停下脚步,目光复杂地看着苏宁。
准许大臣在京城蓄养如此规模的私人武装,这在本朝尚无先例。
B。。。。。。
“准了!”万历终于下定决心,“朕会给你一道手谕。不过。。。。。。”
他盯着苏宁,一字一句道:“这五十人,必须登记在册,每季由锦衣卫核验。苏先生当明白朕的苦心。”
“臣明白。”苏宁深深一揖,“陛下恩典,臣感激不尽。此举既为保命,更为保住变法火种。”
当苏宁退出暖阁时,月色已上中天。
他望着紫禁城巍峨的剪影,轻轻抚过袖中刚刚获得的手谕。
这五十个护卫的名额,将是他推行新政的第一道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