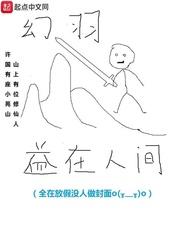笔趣阁>陆地键仙 > 第1320章 情圣(第1页)
第1320章 情圣(第1页)
祖安暗暗擦了擦冷汗,这些真神还真是喜怒无常。
不过马上止住了这些纷杂的念头,免得被那些存在察觉。
翻开手里的《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仿佛大道之音在耳边回响,那一瞬间祖安有无数感悟升起。
体内隐隐多了一种叫浩然正气的东西。
恭喜获得新的秘典《正气歌》,是否吞噬?
这时脑海中响起了久闻的声音,祖安又惊又喜,早有类似。。。。。。
山间的晨雾如纱,缠绕在茅屋檐角,阿禾坐在石凳上,手中竹篮里堆着刚采的野豆荚。她一根根剥开,豆粒落进陶碗,清脆如雨滴敲瓦。一只花斑猫蜷在她脚边,尾巴轻轻摆动,耳朵时不时抖一下,仿佛在听风中的低语。
远处传来脚步声,轻而迟疑,踩碎了落叶。来人是个年轻女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她在篱笆外站了许久,才终于开口,声音像被风吹皱的水面:“您……是阿禾老师吗?”
阿禾没有抬头,只是将最后一颗豆子放进碗里,才缓缓抬眼。她的目光不再聚焦于眼前的人脸,而是落在对方胸口??那里有一道极淡的疤痕,藏在衣领之下,却散发出微弱的情感波动,如同熄灭后余烬未冷的火。
“你母亲死于静默室。”阿禾说,不是疑问。
女子浑身一震,眼泪瞬间涌出。“您怎么知道……我甚至没说过话。”
“你带来了她的气味。”阿禾轻声道,“晒焦的茶壶底,樟木箱里的旧信纸,还有……她最后一次抱你时,心跳比平常慢了半拍。这些都在你身上。”
女子跪了下来,不是出于敬意,而是身体无法承受记忆的重量。她颤抖着打开照片??是一位中年妇女,站在一所小学门口,手里拿着一束蓝铃花,笑容温润如秋阳。
“她教语文。”女子哽咽,“她说,字是有灵魂的,写错一个,就伤了一条命。可他们说她传播‘非标准语义’,把她带走那天,她还在黑板上写着‘爱’字的最后一笔。”
阿禾默默起身,走进屋里,片刻后捧出一只陶罐。她掀开盖子,倒出一小撮灰白色的粉末,洒在石阶前。粉末遇风即散,却在空中停留了一瞬,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女人身影,嘴唇微动,却没有声音。
“这是心引的残渣。”阿禾说,“它不能复活死者,但能留住她们最后的选择。你母亲临终前,没有恨,也没有求饶。她想着你六岁生日那天,你把蛋糕分给了班上最穷的孩子。她为此骄傲到最后一刻。”
女子伏地痛哭,肩膀剧烈起伏,却始终没有发出太大声响,仿佛怕惊扰了什么。良久,她抬起头,眼中泪光未干,却已清明:“我能……带一点这灰回去吗?我想把它撒在她的墓前。”
阿禾点头,用一片树叶包了些许粉末递给她。女子双手接过,郑重收进贴身衣袋,然后深深叩首,转身离去。她的背影渐渐融入林间薄雾,像一句终于释怀的遗言。
猫跳上石凳,蹭了蹭阿禾的手。她伸手抚摸它的脊背,低声说:“你也听见了吧?那孩子的心跳,和她母亲一模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山下世界悄然改变。语言并未消失,但变得柔软而克制。人们开始用指尖轻触彼此手腕来表达关切,用烛光明暗传递情绪,甚至用食物的温度判断对方心境。一座城市试点“无词法庭”,所有判决由陪审团以手势与眼神达成共识,结果冤案率下降百分之七十二。
林远曾寄来一封信,不用文字,而是一段刻录在水晶片上的频率波纹。阿禾用耳贴紧晶体,听见的是小满的笑声、守心碑脉动的节奏,以及一段熟悉的旋律??正是那支“无词之歌”的变奏。她知道他们在问:你还好吗?
她没有回信,只将一片晒干的蓝铃花瓣夹进空盒,托一位过路樵夫带回南园。
某夜,月隐星沉,天地俱寂。阿禾忽然起身,赤足走入屋后竹林。她走得极慢,每一步都像是回应某种召唤。竹叶无风自动,沙沙作响,竟拼出一行看不见的文字,在空气中震荡:
**“门要开了。”**
她停下脚步,仰头望天。十四颗星正缓缓移位,排列成一只睁开的眼睛形状。与此同时,南园方向传来一声低鸣,不是声音,而是大地深处的一次呼吸??如同胎儿在羊水中第一次吞咽。
翌日清晨,小满坐着轮椅出现在山脚,身后跟着林远。两人皆风尘仆仆,眼中却燃着异样的光。
“它醒了。”小满说,“守心树的果实提前成熟了。”
阿禾静静听着,手指摩挲着门框上的木纹。
“昨晚全球共有三千二百一十七人同时梦到同一扇门。”林远补充,“梦里没有出口,也没有入口,只有等待。心理学家统计,这些人在现实中都有亲人死于静默系统。”
“而且……”小满望着她,“果实落地时,喊的是你的名字。”
阿禾闭上眼,片刻后轻问:“你们想让我去吗?”
“我们不敢让你去。”林远声音低沉,“但我们知道你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