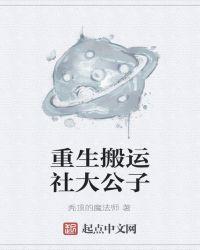笔趣阁>国潮1980 > 第一千六百五十章 好老师(第2页)
第一千六百五十章 好老师(第2页)
挂了电话,她走到院中,点燃第三支蜡烛放入灯笼。这是惯例??每当一个重要决定做出,她都会添一盏光。十年前第一支,纪念周老先生离世;第二支,庆祝“晨读角”进入欧洲校园;这一支,则为了那些尚未出生却注定要接过火炬的孩子。
雨又下了起来。
而在万里之外的新西兰南岛,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室里,十岁的小艾拉正专注地剪着红纸。她的母亲是汉语教师,去年参加过“薪火行动”培训。此刻,母女俩正按照视频教程,制作中式灯笼。
“妈妈,我们能把灯笼挂在图书馆吗?”小艾拉问。
“当然可以。”
“那我能告诉同学们,这是从中国传来的光吗?”
母亲摸摸她的头:“不止是光,更是希望。从前人们点灯是为了读书,现在我们点灯,是为了不让任何人迷失在黑暗里。”
同一时间,贵州山区的那位女教师收到了“墨香斋”寄来的礼物??一套特制拼音卡片,每张背面印有一句经典诗词。她在班上宣布这个消息时,八个学生齐刷刷站起,大声朗读扉页上的字:“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深夜,陈知微伏案撰写《传统书院修复技术白皮书》。写到“材料溯源”一章时,她忽然停笔。窗外月色如洗,照在书桌一角的老照片上??那是十年前她与艾米丽、米晓卉在“益商堂”竣工仪式上的合影。三人站在屋脊下,身后红旗招展,脸上皆有风霜与笑意。
她拿起手机,给艾米丽发去一条语音:“你说得对,灯不怕远。但我现在才懂,最怕的是近处无人守。谢谢你,一直隔着海洋,为我们点着那一盏。”
回复很快到来,是一段视频。画面中,佛罗伦萨的孩子们正将亲手绘制的灯笼逐一挂起,连成一片红色星河。背景音乐竟是用古琴演奏的《茉莉花》,虽不熟练,却情真意切。艾米丽出现在镜头前,怀里抱着女儿,笑着说:“她刚学会写‘中’字。我们决定,明年带她回北京,去看看真正的‘守常居’。”
米晓卉看到这段视频时,正坐在开往山西的高铁上。窗外山河奔涌,朝阳初升。她把视频反复看了三遍,然后打开笔记本,写下新的年度目标:
一、“京灯计划”将在三年内完成百座传统院落修复;
二、启动“青年传承人培养工程”,每年遴选五十名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系统学习古建技艺与文化阐释;
三、与海外华文教育机构合作,建立全球“晨读联盟”,实现跨国同步诵读。
她合上本子,望向远方。铁轨延伸之处,一座古城轮廓渐显。那里有一所等待重生的书院,据说明朝时曾有学子在此苦读十年,终成一代大儒。当地人称其为“望龙门”??意思是,只要坚持向上,终能跃入云霄。
列车进站,广播响起。她拎起行李,深吸一口气。
又一个春天来了。
又一盏灯,等着被点亮。
傍晚时分,赵振国收到一条短信:“承志园”入选国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典型案例。他正在指导两名年轻学徒制作斗拱模型,看完信息后抬起头,对两人说:“记住,你们手上拼的不是木头,是时间。一百年后,还会有人站在这里,指着这根梁说??瞧,这是赵师傅那年教徒弟做的。”
学徒腼腆地点头。其中一个低声问:“师傅,如果将来没人来看这些老房子了呢?”
赵振国放下刻刀,望向院中那株桂花树。春风拂过,细碎花瓣飘落肩头。
“那就让更多人知道它们的存在。”他说,“一个人点灯,或许微弱;但若人人都愿俯身吹一口热气,再冷的夜也能暖起来。”
同一时刻,林婉清正在整理一批新发现的民国教育档案。其中一份泛黄的毕业证书引起她的注意??持有人名叫李承光,籍贯北平,毕业院校正是“夜读庐”。备注栏写着:“品行端正,勤勉好学,尤擅书法,立志兴教乡里。”
她忽然想起什么,翻出“墨香斋”的学员名单,果然找到一个叫李志远的年轻人,备注写着:“李承光之孙,现为河北某县中学语文教师。”
她立即拨通电话。听筒那头,传来略带激动的声音:“您是说,我爷爷当年读书的地方,现在又能上课了?”
“是的。”她说,“你要不要回来,替他再上一节课?”
三天后,李志远踏进“墨香斋”。他穿着朴素,背着一个旧布包。当他走进讲堂,看见墙上挂着祖父年轻时的照片(系档案馆提供),双腿竟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陈知微迎上前:“我们知道您会来。”
他哽咽着问:“我能在这里,给我的学生直播一堂课吗?”
“当然。”她微笑,“这是属于你们的课堂。”
直播开始时,全国两千多名师生在线观看。李志远站在讲台前,翻开一本破旧的《论语》??那是他父亲传下来的,扉页上有三代人的签名。
“今天,”他声音颤抖,“我要讲一句我爷爷最爱的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镜头缓缓扫过空旷的学堂,最终定格在那盏永不熄灭的红灯笼上。
光,依旧明亮。
路,仍在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