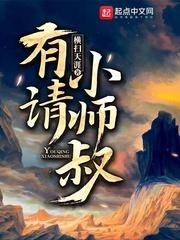笔趣阁>1987我的年代 > 第706章(第3页)
第706章(第3页)
月底,勘察组从怒江返回。带回的照片令人心颤:一道锈迹斑斑的钢索横跨怒江峡谷,两岸悬崖如刀削,江水咆哮如雷。孩子们穿着单薄校服,背着书包,一个个滑下索道,脚下是百米深渊。雨季时,索道常因湿滑停用,学生只能辍学在家。
更严峻的是,当地无稳定电力,通信信号几乎为零,冬季气温常降至零下,建筑材料运输极其困难。
“常规‘渡舟屋’模式在这里行不通。”艾力指着地图说,“我们必须设计一种模块化、抗风抗震、自带能源的新型结构。”
“还要考虑医疗应急。”古丽补充,“上次坠江的女孩虽被救起,但因送医不及时落下残疾。新屋必须配备远程诊疗系统。”
林小满沉思良久,忽然抬头:“我们能不能……把‘渡舟屋’建在索道终点?”
众人一愣。
“就在对岸山坡上,建一栋集教学、住宿、医疗、能源于一体的综合舱。”她迅速在纸上勾画,“用集装箱改造,预制组装,吊运上山。屋顶铺光伏板,墙面嵌保温层,内部划分学习区、休息区、直播室和急救角。”
“可行。”周宇点头,“我认识一家做极地科考站的公司,他们的模块化建筑能在-40℃运行。”
“那就联系他们。”林小满目光坚定,“预算超了,我去筹。”
第二天,她发起了一场名为“为怒江孩子造一间不会塌的房子”的公益众筹。她没有讲故事,只放了一段视频:清晨,六个孩子站在江边,等待父亲帮他们检查滑索的安全扣。最小的女孩只有六岁,手指冻得通红,却笑着说:“我不怕,姐姐说,滑过去就是学校。”
视频最后,黑屏,浮现一行字:“他们不怕,但我们不能不怕。”
二十四小时内,筹款突破八百万。数百条留言刷屏:“请把我名字刻在墙上”“多建一间宿舍,我资助”“我是焊工,需要人手随时联系我”。
林小满一条条看完,关掉页面,望向窗外。秋叶纷飞,鼓楼前的桂花开了,香气弥漫在整个山谷。
她知道,这场跋涉还远未结束。怒江之后,还有凉山、甘南、滇西……那些地图上不起眼的小点,藏着无数双渴望的眼睛。
但她也不再焦虑。因为她终于明白:**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被万千微光簇拥前行**。
十一月初,地坪乡迎来第一场霜。清晨,孩子们在校门口发现了一块新立的石碑,上面刻着“天籁之舟?首航纪”:
>此地曾无声,今有歌如潮。
>
>此屋非砖木,乃心火所铸。
>
>愿后来者,继此灯火,
>
>渡己渡人,舟行不息。
林小满站在碑前,轻轻抚摸字迹。身后,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练习《云端共唱》新曲目的声音,清越如铃。
她转身,走向停在村口的越野车。行李已装好,目的地:云南怒江。
临行前,阿?跑过来,塞给她一封信。信封上画着一艘小船,船上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女子,头顶星星。
她打开信,里面只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老师,我会守好这盏灯,等你回来带我去北京唱歌。”
林小满把信折好,放进胸前口袋,贴近心跳的位置。
车启动,缓缓驶离。后视镜里,“天籁之舟”渐渐变小,最终融入青山之间。
她没有回头。
因为她知道,前方,另一群孩子正站在江边,仰头望着天空,等着那盏灯,照亮他们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