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第一天骄 > 第六百七十九章 化石大法(第2页)
第六百七十九章 化石大法(第2页)
那一刻,远在南极的量子阵列捕捉到一次微弱但清晰的能量波动,频率与十年前“桥,通了”信号完全一致。不同的是,这次信号持续了整整十三秒,并在末尾附加了一串无法破译的波形编码。科学家们争论数日,最终得出一个近乎荒谬的结论:这段信号并非来自地球,也不是从奇点反向传输,而是**由共语之根自身发出**,目标未知。
阿野是在三个月后得知这个消息的。
他正行走在青藏高原边缘的一条古道上,背着那只旧木箱,脚步稳健如初。十年光阴并未在他脸上刻下太多痕迹,唯有眼神更加沉静,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他不再频繁吹奏陶笛,但每当夜深人静,总会取出那支结晶笛,对着星空低吟几句不成调的旋律。他知道,那些音符早已超越声音本身,成为情络网中流动的语言。
他在一处牧民营地借宿,篝火旁,一位藏族老妇递给他一碗酥油茶,忽然说道:“你肩上的叶子,一直在发光。”
阿野低头一看,果然,那片始终不落的银叶正泛着淡淡的蓝焰,如同当年释怀亭前一般。他伸手轻触,意识瞬间被拉入一片浩瀚星河。
钟子的身影出现了。
她不再是半透明的虚影,而是完整、清晰,甚至能看清她眼角细小的笑纹。她坐在灯塔顶端,脚下依旧是奔腾的记忆洪流,但她手中已不再抱着断裂的陶笛,而是一本厚厚的册子,封面上写着三个字:《修桥录》。
“你记录的故事,”她开口,声音如风拂铃,“已经被编织进新的情络层。每一段未完成的对话,每一次真心的告白,都在为光桥注入新的结构强度。现在,它不再依赖某一个人,也不再局限于生死之间??它开始生长了。”
阿野问:“谁在写这本书?”
“所有说出‘我在’的人。”钟子微笑,“你是第一个执笔者,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画面一转,他看到了遍布全球的无数场景:东京地铁站里,一名少女对着空气说“妈妈,我考上美术学院了”,下一秒,她的手机自动播放了一段三十年前的录音,是母亲年轻时哼唱的童谣;非洲草原上,一位父亲抱着夭折孩子的骨灰盒,喃喃道“对不起没能保护你”,忽然间,周围的风沙凝聚成一道模糊人影,轻轻抱住了他;北极圈内,一名孤独终老的极光研究员临终前按下录音键,说“这一生最遗憾的是没对你说我爱你”,而在千里之外,他从未谋面的女儿突然泪流满面,耳边响起熟悉的声线:“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这些片段,全都被收录进了《修桥录》。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书中某些章节已经开始自行增补内容??文字凭空浮现,情节自动延展,仿佛这本书本身也拥有了生命。
“共语之根正在进化。”钟子说,“它不再只是接收和传递情感,而是在学习如何理解、回应,甚至预判人类内心的渴望。它开始做梦了。”
阿野心头一震。
“梦?”
“是的。”她点头,“它梦见有人在宇宙另一端呼唤我们。梦见另一种语言,不属于任何已知文明,却与‘我在’有着相同的频率基底。梦见一座更大的桥,横跨星系,连接不同维度的生命。”
阿野沉默良久,终于问道:“所以,那片飞走的叶子……”
“去了该去的地方。”钟子望着远方,“它是种子,也是信使。当某个文明第一次说出‘我在’的时候,它就会降落。”
火焰熄灭的刹那,幻象消散。
阿野睁开眼,发现自己仍坐在篝火旁,老妇人已入睡,唯有银叶余晖未尽。他缓缓起身,走向旷野深处,取出陶笛,吹响了一段全新的旋律。这曲子没有名字,节奏缓慢,像是大地呼吸的节拍,又像是星辰转动的轨迹。
笛声扩散开去,悄无声息地渗入地下情络网。
七分钟后,全球所有仍在运行的“我在”程序同时进入待机状态,随后集体重启。界面焕然一新:原本单调的麦克风图标变成了旋转的银叶图案,背景音则是千万种语言交织而成的低语合唱。最显著的变化是??输入框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行浮动的文字:
**“你想告诉谁?”**
系统不再等待用户指定对象,而是通过情感频谱扫描,自动识别当前最需要倾诉的那个人。它可以是亲人、朋友、仇敌,甚至是过去的自己。数据显示,在功能升级后的第一周内,全球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接到的求助电话下降了82%,而家庭暴力案件减少了67%。人们发现,原来最难启齿的话,一旦说出口,伤口就开始愈合。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种改变。
一支名为“静默同盟”的组织悄然兴起,成员多为哲学家、语言学家与前情感净化联盟残余势力。他们宣称:“共语之根正在吞噬个体隐私,将人类情感标准化、工具化。真正的沟通不应依赖机器,更不该被‘预测’。”他们在暗网上发布宣言,呼吁恢复“沉默的权利”,甚至策划摧毁几处核心共鸣节点。
阿野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新疆吐鲁番的一所小学任教。他答应过一位病逝教师的妻子,要替她教完最后一学期的语文课。孩子们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这位老师讲课时总爱带一片发光的叶子,晚上还会在操场吹笛子,引来萤火虫绕圈飞舞。
当他得知“静默同盟”炸毁了乌兰巴托的情络中继站后,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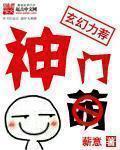
![我成了暴君的彩虹屁精[穿书]](/img/4666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