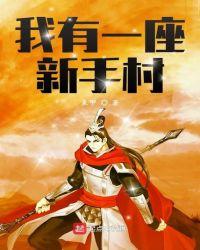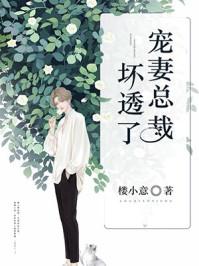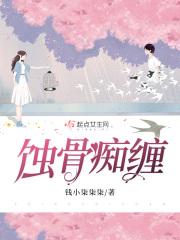笔趣阁>我在古代当孝女 > 布坊变化(第1页)
布坊变化(第1页)
自从回了村,陈萱家就没少了热闹,陈萱不耐烦应付,躲去了族长家,王春花和陈传根则是乐在其中,每日在村里与族人闲谈,快活极了。
这几日,又张罗着要把旧屋推了重建,起个气派的院子,这个提议陈萱倒是不反对,这儿是陈氏族地,又接手了陈氏布坊,日后回来的日子不会少。
因着旧屋要重建,王春花和陈传根又不愿去别人家将就,就先回了县里。
莫三喜做了布坊的管事,也就和陈萱一样留在了陈家村,陈萱请村里人在布坊旁边盖几间屋子,留一间给三喜住。
布坊坐落的位置属于陈家村,买地皮很容易,这几间小屋盖得就很是宽敞。
望着布坊里新起的几间气派屋子,坊里众人都明显感觉到布坊真的不一样了。
陈传顺就是其中一员。
他是布坊的老织工了,从十岁起,就在坊里做学徒了,布坊易主的事,起初他很忐忑,
怕萱丫头把布坊给折腾没了,只是不想短短几日,布坊的变化可是说是把黄历撕得粉碎,拿狗血重新写了。
首先是坊里包饭了。以前一日的午食,是让家里那口子做好了送来,吃的什么那就是有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了,反正陈传顺是家里不富裕,年景不好的时候,碗里的水都能照见人的影子。
现在那可不一样了,隔壁的大厨房,每到饭点,飘出来的香味叫他总忍不住咽咽口水,还得小心翼翼的,生怕被同屋的织工听见,那多丢人啊,只是,眼神向周围一撇,明显看到一旁一起织布的陈家旺喉结一滚。
没一会儿,又传来“咕噜”一声,大家都在理线,所以屋里格外安静,衬得这声响分外明显,陈传顺和同屋的织工不约而同地看向声源处。
陈家木的脸瞬间爆红,大家都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
陈传顺心中得意,他早在意识到自己饿了时,就借着织布的动作,用手肘抵着肚子,就怕发出声音,木哥儿年纪小,可没他们这些老人经验足。
随着香味越来越浓,“砰——”厨娘敲了声啰,意味着开饭的时辰到了。
就见一屋子织工迅速给线打好结,做上记号,方便下午从这儿继续,就迅速走出房门,动作一点是也不拖泥带水地往外走。
在去厨房之前要先去另一间屋子拿自己的碗,这间屋子里全是一排排的小柜子,长宽和手肘一致,布坊的每一位工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柜子,用来放自己的四人物品。
刚建的时候,陈传顺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现在可喜欢了,他的柜子是最规整的,放着水壶、碗、以及一件外杉,这是一日里天气变化,将人冻坏了。
曾经坊里没放东西的地方,织工们要么忍着燥热一直穿上,要么自己随便找个地,没个保障。
陈传顺可宝贝他的柜子了,每七日休沐前,都得自己用帕子擦擦,务必不让柜子沾染一丝灰尘,有人提出想跟他换个柜子,他看一眼对方的柜子,想也没想就拒绝了,对方的柜子里还有没弄干净的油,如何能和他的柜子比。
他熟练来到第三列柜子第二排第四个柜子前,看到下方用红色的颜料标记的“叁贰肆”,确认是自己的柜子才用钥匙打开上面的小锁,把自己的碗和水壶拿了出来。
碗和水壶都是坊里发的,听说每季只各发一个,打碎了只能自己用工钱买,陈传顺拿的动作就格外小心翼翼,下一季的,他想留着给家里那口用,这样下地时就可以自己带水壶,不用自己回家喝了。
拿上碗和水壶,陈传顺就往厨房走去,或者应该叫“食堂”,这是莫管事的喊法,他们还没习惯呢。
食堂里已经有些人了,陈传顺从善如流的排队,先去排米饭,食堂的饭可不像家里,就是在上面立根筷子,也不会倒。
排完米饭,陈传顺就去排红烧肉的队伍,食堂每日一荤三素,想吃什么自己去排队打,唯一的要求是不能浪费,每日都有厨娘在门口检查碗里是否有剩。
若浪费次数多了,坊里可是会辞人的,工人们一听哪里还敢浪费,这样的好工是找破天也找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