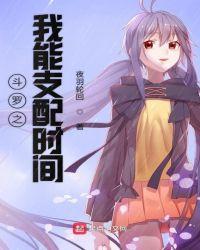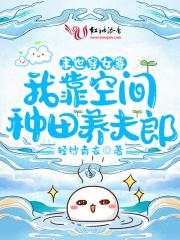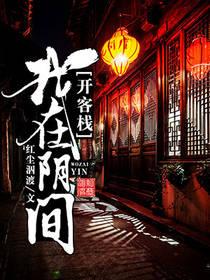笔趣阁>红楼之黛玉长嫂 > 196第 196 章(第4页)
196第 196 章(第4页)
黛玉点头:“嗯。你说,他会来看我最后一面吗?”
话音刚落,门外传来熟悉脚步声。
一个苍老却稳健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手中提着一只竹篮,装满新鲜莲藕与菱角。
“听说你喜欢吃这个。”周砚之笑着说,“我在姑苏采的,连夜赶来。”
她望着他斑白的鬓角,忽然泪如雨下。
他走过来,握住她的手:“我不是说过吗?只要你还在,我就一定会回来。”
她靠在他肩上,喃喃道:“我累了,砚之……我真的撑不住了。”
“那就歇一会儿。”他轻抚她的背,“我在这里,一直都在。”
三天后,她最后一次巡视明慧书院。学生们列队相迎,齐声背诵《法典》第一条。
一个小女孩跑上前,递给她一朵野花:“先生,这是我从山上采的,叫‘不死草’,风吹不折,雪压不断。”
黛玉接过,含笑点头。
回到府中,她写下遗书:
“吾死之后,勿哀勿悲。将我骨灰撒于女子先贤祠梅林之下,与那些未曾相识却同路而行的女孩们作伴。
《法典》交予沈素衣执掌,柳青鸾协理,霍七娘护法。
每年七月初七,全国女子书院停课一日,诵读法典序言,铭记来路艰辛。
若后世有女子受困,望有人挺身而出,如我当年一般。
纵我不见,魂亦护之。”
七月十五,中元之夜。
她躺在床榻上,窗外细雨霏霏。紫绡握着她的手,低声唱起江南童谣。
她微微一笑,仿佛看见母亲站在灯下缝衣,嘴里哼着同样的曲调。
“娘……”她轻唤一声,“我回来了。”
雨声渐歇,月光破云而出,洒在庭院梅枝上,花瓣飘落如雪。
檐角铜铃轻响,似有风来,又似有人离去。
翌日清晨,长安百姓闻讯奔走相告。无数女子手持灯笼,走上街头,默默行走,汇成一条无声的河流。
皇帝亲赴府邸吊唁,敕令全国斋戒三日,降半旗致哀。
而在遥远的草原,阿依娜点燃九堆篝火,率领万名女子跪拜南方。乌兰将军拔剑划地,立碑铭志:“此生追随昭德之道,至死不悔。”
多年以后,当《女子权益法典》成为国之根本,当女子为官如雨后春笋,当小女孩们背着书包走进学堂,人们仍会讲起那个名字??
林黛玉。
不是柔弱多愁的闺秀,而是劈开黑暗的第一道光。
她的墓碑上没有生卒年月,只刻着一句话:
“她曾相信,女子也能照亮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