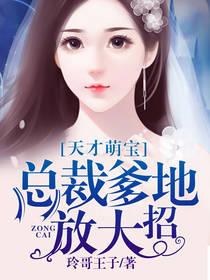笔趣阁>我魂飞入红楼梦 > 第二十八章(第1页)
第二十八章(第1页)
听到贾琏和一名老嬷嬷谈到“咱们家要迎来大姑奶奶”的话,凤姐儿接着感慨道:“果真那样,那我也可算见了个大世面了!”随即,凤姐儿似乎又感到了自己的“生不逢时”:“哎哎,要是我早出生二三十年,如今的这些老人家也不会瞧不起我没见过大世面了。要是说起太祖皇帝仿效舜帝南巡的事迹,真比一部书还要热闹,我偏偏出世晚了,没能赶得上。”
老嬷嬷似乎更得劲儿了,道:“哎呀,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喜事啊。那时候我大概才五六岁,刚刚长记性。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整治海塘海滩,只预备了接圣驾一次,把银子花得如淌海水似的。哎呀呀,那真是,说起来……”
听到这里,凤姐儿忽然觉得,老嬷嬷把贾府说得如此显耀荣光,似乎一下子黯淡了她王府了。娘家家族的被比下去,于凤姐儿来说,在情感上是绝对难以接受的。于是她没等老嬷嬷说完,便连忙抢过话头说:“我们王府也预备接驾过一次的。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是有外国人过来,都是我们家接待养活他们。粤、闽、滇、浙等等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老嬷嬷对凤姐儿的抢夺话题心生了一点感觉,但马上便尽量附和起凤姐儿来,道:“那是哪个不晓得的?到如今,还有句俗话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哦,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哎呀呀,那气派,他们家共接驾了四次,四次呀!要不是我们亲眼望见,哪个相信啊?别说银子成了粪土,就是世上其它的奇珍异宝,哪一样不是堆积如山的?”
凤姐儿道:“我们曾听见我家太爷说过,也是这样的情况。我真是有点儿奇怪:他们家怎么就那么富贵的呢?”
老嬷嬷道:“哎呀,还不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不是好像有这句话的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正一切都是皇帝佬儿家的,其他人家哪有这么多钱买那么大的热闹啊?”
凤姐儿道:“这就对了。”——两个人达成了共识,真英雄所见略同也。当然,有时候,狗熊间的识见,可能更趋向一致。
……在后来被命名为“大观园”的省亲别院的建造之前,是举行了最高级别的家族要员“会议”的。参加“会议”要员资格的认定,虽然没有书面的“文件”作出规定,但却有一双看不见的无形的大手在操纵。一、参加者首先必须得是男性。像凤姐儿这样虽然具有日常工作的权力,但仍然没有参与决策建造省亲别院的最高级别会议;二、参加者必须得是成年人。这个“成年人”的定义不是像后人之后人以十八周岁为界的,而是以结婚与否为界。宝玉虽然是老祖宗嫡亲的孙子,王夫人唯一在世的儿子,但因为还没有结婚,所以也不曾有资格参与讨论。至于哪几个人参与了讨论,或有人只是参加了半程的讨论,宝玉也不得而知。不过,他即便知道了,也未必感兴趣。
贾敬本是具有参与决策的资格的,只可惜他的整个心思都放在修道祈寿方面,所以属于“自动弃权”。贾政当然是家族核心人物之一,但是除了读书和官场运作之外,他在房舍、园林的选址、设计和建造方面,专业知识是极为匮乏的。所以他虽然参与了讨论,但其所发言的内容,几乎不到三句话。当然,他一点儿也没有因之而感到被冷落或自卑,相反,他把这一切视为“俗务”,内心深处确有一股不屑的意味。
所以,在建造大观园这项伟大且神圣工程的问题上,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人物可能是贾珍。从选址、筹措银两、请工匠,到运载木料、砖瓦、石灰,一直到夯实地基正式建造,贾珍参与了整个的过程。包括是确定做“热工”——全天管工匠们和辅助工们三顿饭,还是做“包工”——增加工匠及辅助工的工钱,但只要中午供应一顿简餐,贾珍都参加了讨论和拍板。
省亲别院的地址选在东府花园的东边,然后再向西北一带延伸、拓展。经过丈量,计算,共有三亩半多的土地。决策者们认为,这基本上达到要求了。
最高决策会议的第二天,就传请设计师画图设计了。因为这项工程,除了神圣而伟大之外,还具有相当的迫切性:因为据传来的消息,周贵妃的父亲已经在家里正式动工建造省亲别院了。另外,吴贵妃的父亲也行动迅速。所以,如果迟迟不动工,就会明显的被别家比下去,这显然比后人之后人输掉了科学或艺术的竞争还要后果严重。
图纸设计定稿之后,后面有几项工作几乎是要同时进行的:一、挖沟挑土,引来活水;二、堆土成丘,搬运石头建造假山;三、运送木头、砖瓦、石灰等等。
不管是做热工,还是做包工,开工酒是必喝的。所有参与工程的建设者都尽自己所能喝足吃饱,美酒和大肉增强了他们的力量和精神、士气。
打地基开始了!打地基者分成了三个小组,每组八人。每个小组都是两条汉子扶住夯把子,四条汉子用粗绳索使劲儿拉起大夯,然后再一齐放松,让大夯猛的砸下去,使地面变得结结实实,足以承担楼房或亭阁的重量。随着一阵阵“嗨吆”“嗨吆”的声音,大夯被拉动而“蹦跳”着,不断前进和扩展着坚实地基的面积。
最为热闹的恐怕要数主建筑架上正梁的那一天。那天,前来祝贺的达官贵人家就有十几户,都用红布或红袋子包了一定数量的银子,贾府照例的热情招待了每一位来客,在此不一一记述。就在那一天,几乎全家族的人都前往观看这千载难逢、前所未有的盛事。一名杰出的木匠代表站在那高高的支撑架上,手握一柄斧头,给那正梁钉牢一根根铁钉,一边钉着钉子一边“说歌子”:“梁上祥云腾锐气,家中喜气绕门庭。今日上梁大吉庆,来日安居福满盈!”“天光照亮新房顶,富贵喜乐伴人行!”“欢声笑语迎上梁,荣耀之光照四方!”等等。当给正梁钉完最后一根钉子扔下斧头时,工匠代表说道:“斧头落地口朝上,敬祝皇上万寿无疆!”于是所有观看的人都欢欣鼓舞,欢声雷动,欢天喜地。
宝玉站在人群之中,他多么想跟黛玉靠在一起,说说话儿,可是他望见父亲站在他不远的前面,感觉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回过头来,查问他功课学得怎么样,于是他并不能全身心的自由自在,只能规规矩矩的站在原地,不敢向黛玉那儿挪动。别说看见,宝玉哪怕只是联想到父亲的影子,心中即刻就会产生阴影。
……虽然没有正式形成家族发展纲要和行动计划之类的书面文件,但依据最高家族要员会议的讨论结果,还有一件较为重要的事情已经到了需要行动的时候了。贾珍把这件事交给了贾蔷。贾蔷随即组织了一支小队。如果贾蔷自己是组长的话,则组员有赖管家的两个儿子,还有单聘仁、卜固修两个清客等。这件事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这三项:一、请聘教习;二、采买女孩子;三、置办乐器行头等。要在贾府内组成一个高水准的歌舞艺术团体,这些事情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
贾蔷前来跟贾琏通报这些情况。因为贾琏长一辈,所以说是前来向贾琏回报情况,也是未尝不可的。可是贾琏对贾珍的用人是否得当即贾蔷的能否胜任持怀疑的态度,或许,内心还滋生了那么一点点嫉妒。
贾琏用怀疑的眼光仔细打量了贾蔷好长时间,然后笑着说:“做这些事,你在行吗?这件事虽然不是很庞大,但从里头多多少少也是可以捞点儿油水的。换句话说,这里头也是有点儿术头儿的呢。”
贾蔷略带腼腆的道:“任何事就跟大姑娘坐花轿子一样的,总有个头一回啊。——我学着办就是呢。”
这时候是在晚上。如果不是门内的灯光投射到外面的话,那外面简直就是漆黑一片。贾蔷、贾蓉——贾蓉是随着贾蔷等人一起过来的——、贾琏、凤姐儿等人就站在靠在门口的地方说着话儿。因为贾蓉没有被分配去姑苏办事,他仍被留在贾府之内专门负责打造金银器皿之类的事情。于是在贾蔷跟贾琏、凤姐儿谈论往姑苏办事方面的话题时,于贾蓉几乎没有了关系。这时候的贾蓉几乎无事可做,无话可说。无所事事的聪明伶俐的贾蓉这时候看准了凤姐儿的身后是一片漆黑,同时也注意到贾琏的注意力几乎完全倾注在贾蔷身上。于是贾蓉便觉得有机可乘了。他悄悄的行移到凤姐儿身后的黑暗之中,用手轻轻拉动凤姐儿的衣襟,从而获得小甜蜜。
凤姐儿也察觉到贾蓉悄悄移到她身后了,更是感觉到了贾蓉在轻轻拉动她的衣襟。但是,现实的环境不允许她丢开贾琏等而让她跟贾蓉嬉戏快乐。于是她只能装着丝毫不知情。她轻轻的摆动了一下手,并没有触碰贾蓉,而是向贾琏面前靠近了一点儿,批评起贾琏对贾蔷办事能力的疑虑以及对贾珍用人是否恰当的怀疑。她道:“你也太操闲心思了!难道大爷比咱们还不会用人吗?偏你就怕他不在行!哪个都是在行的?孩子们都长这么大了,没有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子跑?也没听过猪子叫?——大爷派他去,也不过是挂过帅旗儿的,哪里是叫他认真的去讨价还价、具体的做经纪计算的呢?依我说,这是郑家娶何家姑娘,——郑何氏(正合适)!”
贾琏对贾蓉在凤姐儿身后的小动作当然是毫无所知的。贾琏对凤姐儿道:“你说的这道理也是自然的。我哪里是要推翻掉这个安排啊,我也是在替他筹算筹算呢。”他的脸转向贾蔷道:“这一项支出的银子是如何安排的呢?”
贾蔷回答道:“刚才自然议到这一层的。没得银子哪能办事呢。管家赖爷爷说:不需要从京城带银子去。江南甄家还收存着我们家五万两银子呢。我们只要带一张汇票去,先支取三万两,还有两万两仍然暂时存放在那里。后面置办花烛彩灯及各色帘帐什么的可能就要用到了。”
贾琏称赞道:“这个办法好。不然,还要一路上带上几万两银子。”他想到了沿途带几万两银子似乎具有某种危险。但是,他没有说出口。他觉得如果说出口了,似乎有点不吉利。
凤姐儿忙转向贾蔷道:“这么着吧,我们这里有两个办事稳当的人,你就带了他们去办。”
贾蔷笑着说:“正好,真是瞌睡时得到了枕头。我担心人手可能不够,正想跟婶婶讨要两个人的。——婶婶准备派哪两个人跟我啊?”
凤姐儿约略思考了一下。平儿和老嬷嬷提示说:“一个叫赵天梁,一个叫赵天栋。”
凤姐儿道:“对了,你们可别忘了。——我去干我的了。”说完,便大步流星似的走开去了。
贾蓉装着好像有什么重要事情似的,跟着凤姐儿走了过来。他紧走了多步,到了凤姐儿的身旁,悄悄的笑着说:“婶婶你需要什么,开个账单儿让他们带去,按着账单儿置办回来。”
凤姐儿一下子就明白了贾蓉的意图,笑着轻轻的“呸”了一声,道:“真放你的狗儿屁!你是想用我的名义让你自己得好处呢!你就喜欢那鬼鬼祟祟的做事!”说完,朝贾蓉一笑,便离开了。
贾蓉看着凤姐儿的背影,想:“看什么时候,我乘个空儿,×你!”
贾蓉又回走了过来,跟贾琏等又商量了几句姑苏之行所要办的事。